第三章:渡劫之路
孟蝉几番推拒无果,也只好看着人进了灶房,煎药煮粥,殷勤地忙活起来。
那边两个青衣小婢熬着药,这头染儿便将孟蝉扶到床上歇息,替她脱去鞋袜,细细查看她腿上的伤势。
孟蝉有些尴尬:“已经无恙了,劳烦你家小姐挂念了,再过不久就能照常走路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染儿看了许久后,抬头笑吟吟道:“小姐满心歉疚,只盼望孟姑娘能早日好起来,这不,还特地带了宫中御医开的珍稀药材来,孟姑娘待会儿就喝一碗,对腿脚扭伤保准大有裨益。”
孟蝉面露犹疑:“药就不必了,付府之前就送了各种药过来,我每天也在吃,只怕会相冲。”
染儿笑意不减:“孟姑娘不用多虑,小姐都向御医问好了,几味药材不会相冲,她这次是真心想弥补。若是孟姑娘不放心,等药熬好了,奴婢可以先尝一口,不知孟姑娘意下如何?”
孟蝉面皮薄,赶紧摆手:“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染儿却已扭头看向床边的初一,柔声笑道:“小公子,劳烦去灶房看看,那药熬好了吗?”
初一双手抱肩,小大人一般撇撇嘴,奶声奶气道:“你怎么不自己去看,你没长腿吗?”
染儿一时哑然,孟蝉赶紧将初一一把搂过,捂住嘴:“没礼貌……就去看看吧,正好姐姐也有些话想跟人说。”
待到初一气哼哼地出了门,孟蝉才望向染儿,将脱去鞋袜的双脚缩了回来,有些不自在道:“染儿姑娘,你不如跟我说实话,你家小姐……究竟想干什么?”
灶房里药香扑鼻,灶上的药罐子冒着腾腾热气,两个青衣小婢耳尖竖起,听到那脚步声由远至近而来,赶紧清清嗓子,闲话家常般聊了起来。
“哎哎,你听说了吗?这场长街论礼一结束,咱们府里就要办喜事了。”
“办什么喜事,难道是少爷……要娶那位孟姑娘吗?”
“当然不是了,少爷是什么人,怎么可能自降身份娶一个入殓馆的妆师呢?”
初一脚步一顿,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小小的个头隐入门边,扒着门缝听那里面传来的对话——
“那是……要娶咱们小姐了?”
“可不是,昨夜太子殿下来了一趟,把小姐也叫去了,说让少爷在长街论礼上好好表现,如果胜了那天玑国,他便亲自做主,给少爷和小姐主婚,让他们再续前缘,叫付府喜上添喜。”
“真有这回事?那少爷怎么说?”
“当然是真的了,我就在小姐旁边奉茶呢,太子亲口说的,还能有假?少爷自然也是高兴的,他跟小姐本来就是一对,如今能得天恩,再续前缘,岂不比什么都好?”
“难怪少爷这么紧张这次长街论礼,每天准备到深夜,原来是为了讨个恩典,同小姐再续前缘啊。”
“正是如此,此刻论礼估计已进行到一半,少爷成竹在胸,定能获胜。待到论礼结束后,小姐便能得太子殿下的恩典,名正言顺地跟少爷在一起了。”
孟蝉几番推拒无果,也只好看着人进了灶房,煎药煮粥,殷勤地忙活起来。
那边两个青衣小婢熬着药,这头染儿便将孟蝉扶到床上歇息,替她脱去鞋袜,细细查看她腿上的伤势。
孟蝉有些尴尬:“已经无恙了,劳烦你家小姐挂念了,再过不久就能照常走路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染儿看了许久后,抬头笑吟吟道:“小姐满心歉疚,只盼望孟姑娘能早日好起来,这不,还特地带了宫中御医开的珍稀药材来,孟姑娘待会儿就喝一碗,对腿脚扭伤保准大有裨益。”
孟蝉面露犹疑:“药就不必了,付府之前就送了各种药过来,我每天也在吃,只怕会相冲。”
染儿笑意不减:“孟姑娘不用多虑,小姐都向御医问好了,几味药材不会相冲,她这次是真心想弥补。若是孟姑娘不放心,等药熬好了,奴婢可以先尝一口,不知孟姑娘意下如何?”
孟蝉面皮薄,赶紧摆手:“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染儿却已扭头看向床边的初一,柔声笑道:“小公子,劳烦去灶房看看,那药熬好了吗?”
初一双手抱肩,小大人一般撇撇嘴,奶声奶气道:“你怎么不自己去看,你没长腿吗?”
染儿一时哑然,孟蝉赶紧将初一一把搂过,捂住嘴:“没礼貌……就去看看吧,正好姐姐也有些话想跟人说。”
待到初一气哼哼地出了门,孟蝉才望向染儿,将脱去鞋袜的双脚缩了回来,有些不自在道:“染儿姑娘,你不如跟我说实话,你家小姐……究竟想干什么?”
灶房里药香扑鼻,灶上的药罐子冒着腾腾热气,两个青衣小婢耳尖竖起,听到那脚步声由远至近而来,赶紧清清嗓子,闲话家常般聊了起来。
“哎哎,你听说了吗?这场长街论礼一结束,咱们府里就要办喜事了。”
“办什么喜事,难道是少爷……要娶那位孟姑娘吗?”
“当然不是了,少爷是什么人,怎么可能自降身份娶一个入殓馆的妆师呢?”
初一脚步一顿,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小小的个头隐入门边,扒着门缝听那里面传来的对话——
“那是……要娶咱们小姐了?”
“可不是,昨夜太子殿下来了一趟,把小姐也叫去了,说让少爷在长街论礼上好好表现,如果胜了那天玑国,他便亲自做主,给少爷和小姐主婚,让他们再续前缘,叫付府喜上添喜。”
“真有这回事?那少爷怎么说?”
“当然是真的了,我就在小姐旁边奉茶呢,太子亲口说的,还能有假?少爷自然也是高兴的,他跟小姐本来就是一对,如今能得天恩,再续前缘,岂不比什么都好?”
“难怪少爷这么紧张这次长街论礼,每天准备到深夜,原来是为了讨个恩典,同小姐再续前缘啊。”
“正是如此,此刻论礼估计已进行到一半,少爷成竹在胸,定能获胜。待到论礼结束后,小姐便能得太子殿下的恩典,名正言顺地跟少爷在一起了。”
“这真是天大的喜事……不过,里间那位孟姑娘,少爷预备怎么打发?”
“嘘,小点声,那孟姑娘少爷自会有补偿,你看,今儿个小姐不就让咱们来了吗?”
“难怪,少爷与小姐实在仁善,只盼这场论礼快快结束,能够……”
“砰”的一声,对话戛然打断,两个青衣小婢惊恐万分地看向门边,初一小小的个头,一脚踹开了门,周身像笼了一团火般,双眸盛满怒意:
“你们在胡说些什么,爹爹是要娶我娘亲的,才不会娶那个坏女人呢!”
2.长街论礼
孟蝉正与染儿在房中交谈之际,忽然听见初一的怒吼,遥遥从灶房那边传来——
“他就是我爹,就是我爹!”
一阵哐哐当当的声音响彻院落,孟蝉一惊,刚至窗边,便见初一怒气冲冲地从灶房跑了出来,身后两个青衣小婢拉都拉不住。
“小公子快回来!”
“我这就去找爹爹问清楚!”
初一浑身像带了团火一般,头也不回地向外掠去,那两个青衣小婢更加惶恐了:“小公子,快回来,可不能破坏了这长街论礼呀!”
“什么狗屁长街论礼,我才不管,我就要去找爹爹问清楚!”
孟蝉大惊,再顾不得许多,拖着一瘸一拐的腿,推开门就想阻止初一:“快回来,初一,别胡闹!”
但那团怒气冲冲的红影哪里停得下来,一心只想找到付朗尘问个清楚,甚至砸了那长街论礼才好。
等到孟蝉忍痛追出去,两道身影齐齐消失在门边时,青衣小婢们才收起惶恐的模样,聚到染儿身侧,三人望着长街深处,同时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来。
街上人头攒动,侍卫严守,高台外被围得水泄不通,百姓们抻长了脖子,瞻仰这场难得一遇的盛事。
太子端坐首席,两侧分别坐满了官员贵胄,慕容钰、叶书来也赫然在列,就连那袁沁芳,都得了太子特许,占了一方席位。
众所瞩目下,付朗尘身姿笔挺,负手面向台下,气度俊雅无双,正说到东穆严谨分明的律法。
“此第三条,若在春祭、宗庙之祭等重大场合上,有宵小作乱,破坏国运,视社稷威仪为无物者,轻则当场射杀,重则满门获罪。曾有伯阳侯稚子,于祭天之时醉酒闹事,后满朝文武求情,皆不得赦,帝夺其爵位,流放西北,只因祖宗之法不可废,千秋之礼不可乱,这便是东穆自古安邦的基石所在,泱泱大国,以法治民,即便是天子犯法,也将与庶民同罪……”
满场正听得入神之际,台下忽然传来一阵喧闹,苗纤纤也被调来侍卫队帮忙,闻声扭头望去,不由得一惊:“初……初一?”
那满脸怒意,胡闯乱撞,挤进人群里的小不点儿,不正是孟蝉的弟弟——小初一吗?
但苗纤纤还来不及出声,那道红影已经奋力拨开人群,冲着高台之上大声喊道——
“爹,爹,你不要娘亲和初一了吗?”
论礼被骤然打断,满场皆惊,付朗尘更是瞬间煞白了一张脸,猝不及防,而台下的初一还在喊着:“爹,你是不是要娶那个坏女人,你不要我和娘了吗?”
席上的慕容钰和叶书来皆认出初一来,脸色同时一变,旁边的袁沁芳也与众人一同露出吃惊模样,美眸深处却流露出一丝喜色。
侍卫们纷纷围上来想拿人,却都被初一灵巧闪过,他看起来个头小,力道却奇大,身上还似有灼热之气,竟让人一时近身不得。
全场被这一搅,犹如石破天惊,彻底炸开了锅。
首席上的太子面色铁青,拂袖猛一拍:“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把这小孩带走!”
苗纤纤飞身一掠,落在初一身旁,拉过他就想冲出人群外,却被初一狠狠甩开了手,他依旧不管不顾地往台前挤,眼里只有一个付朗尘。
“爹,爹,你快说啊……”
就在一片混乱之际,天玑王子站了出来,抬手一声制止:“通通都住手,把话问清楚再拿人!”
满场侍卫一顿,天玑王子看向付朗尘,扬起一个浅笑:“付大人,你这又是在哪儿惹出的风流债,摘都没摘干净,也敢上台来论礼?”
他先前全程唇舌被制,处处被付朗尘压一头,此刻好不容易逮到了机会,怎会轻易放过。
付朗尘岂不知他所想,深吸口气,已从最初的震愕中回过神来,昂首沉声道:“一个毛头小孩胡言乱语,也能作数吗?”
“哦?”天玑王子饶有兴致,“那你就是不认得他了?”
他扬手一指,对着台下的初一问道:“小孩,你说他是谁?”
初一见付朗尘竟真有不认他的意思,更加着急了,张口便道:“是我爹!”
付朗尘一阵眩晕,面上却强自镇定下来,厉声道:“一派胡言!”
初一眼圈都红了:“我没有骗人,你明明就是我爹,是你把我生下来的,你现在不认了吗?”
话一出口,全场震惊,首座上的太子更是霍然站起,远处赶来的孟蝉恰好听见这一句,瞬间脸色惨白,拖着血淋淋的腿,一把拨开人群:“初一,不要胡说!”
所有目光齐刷刷射来,孟蝉紧紧搂住初一,额上已渗满了冷汗,唇无血色。
慕容钰与叶书来也登时站起,惊呼出声:“孟蝉!”
苗纤纤更是紧张地扑上前,伸手就想去撕衣角替孟蝉包扎:“你的腿,你腿上的伤全裂开了!”
一片乱哄哄中,那天玑王子忽地拊掌大笑:“有趣,有趣!”
他目光骤然向付朗尘一剜,寒意逼人:“此前便听闻付大人浴火重生,乃是得一贵人相助,想必这贵人,便是台下这位姑娘了。但却不知其中还有这诸多隐情,不知今日长街论礼,付大人愿否说与在场众人听听?”
话才落音,付朗尘还未反应过来,孟蝉已经一个激灵,拉着初一便“扑通”跪了下去,忍痛开口道:“不,不是的,此事与付大人无关,这是民女的弟弟,年幼不谙,口出胡言,冲撞了使团与太子殿下,还望诸位大人恕罪!”
初一在孟蝉怀中拼命挣扎着,嘴巴被捂住了还不住呜咽个不停,他力气虽大,却不忍伤到孟蝉,只能不依不饶地含糊喊着:“爹,爹你快说话啊,你不要娘亲和初一了吗……”
台上的太子再也忍不住,几步上前,怒喝道:“快快快,快把这两人带走!”
那天玑王子却一抬手:“不急。”
他依然看向付朗尘,目光灼灼:“太子殿下少安毋躁,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付大人怎么也该给个说法吧。”
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付朗尘暗自捏紧手心,努力不去看向台下的孟蝉与初一,只是向那天玑王子走近一步,冷声道:“台下这位孟姑娘确是下官救命恩人,但也诚如她所言,幼弟无知,顽劣胡言罢了。世间阴阳有道,男子怎么可能会怀孕,难道天玑国中,公鸡也能下蛋不成?就算下官真的承认了,王子又敢信吗?”
这话反将了天玑王子一军,台下百姓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发出笑声来,表示闻所未闻,但高台之上却有两人心中暗自一惊。
这两人,正是慕容钰与叶书来。
他们不约而同想起什么,对视一眼,在彼此眸中,同时瞧见了那日吉祥斋楼上,那个戴着头纱、古怪大肚孕妇的模样。
台上的天玑王子听了付朗尘的话后,也不恼,只是依旧笑道:“哦,按照付大人这么说,那便是这小孩胡言乱语了。”
“正是。”
“很好,那既然是胡言构陷,玷污了朝廷命官的名声,又冲撞破坏了今日的两国论礼,不知按照东穆律法,该当何罪呢?”
此话一出,付朗尘刹那间明白过来,瞳孔骤缩。
那天玑王子却还在高声笑道:“正巧付大人方才还在侃侃而谈,说那东穆律法第三条,若在春祭、宗庙之祭等重大场合上,有宵小作乱,破坏国运,视社稷威仪为无物者,轻则当场射杀,重则满门获罪,不知本王子有没有记错,付大人还说了个伯阳侯之子的故事,可与现下这番情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呀,付大人说是也不是?”
冷汗自付朗尘额上渗出,他背在身后的手握得更紧了。天玑王子却盯着他,继续笑道:“付大人不必紧张,这法理之外,不外乎人情嘛。本王子也非铁石心肠之人,既然台下这位孟姑娘曾对付大人有恩,那么付大人大可网开一面,本王子也可顺水推舟,当作没这回事发生过,咱们照常论礼辩法,付大人觉得怎么样?”
他这话绵里藏针,用意实在恶毒,太子殿下当即站出:“东穆律法森严,绝无包庇一说,王子不必如此!”
“哎,太子殿下言重了。”天玑王子抬手一笑,望着付朗尘似乎十分仁厚般,“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此事与付大人有关,当由付大人来决断才行。”
三言两语间,他便轻而易举,将付朗尘与一杆秤架在了火堆之上。
那秤的一头站着孟蝉和初一,另一头站着整个东穆律法,付朗尘进退维谷,被逼得顷刻之间就得做出选择。
众目睽睽之下,那身俊挺朝服一动未动,生平第一次哑然,他终将目光落在了台下的孟蝉与初一身上。
孟蝉的腿还在汩汩流着鲜血,苍白的脸上满是冷汗,遥遥对视的双眸中却写满了共进退的决心。
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一向大大咧咧的苗纤纤也慌了,按住腰间刀的手都在颤抖:“付……付大人,小孩子不懂事胡说罢了,我现在就把他们带走,现在就带走……”
台上的叶书来眸光一紧,正要开口,孟蝉已经摇摇头,对苗纤纤低声道:“已经晚了,纤纤你快松手,别把你再卷进来了。”
苗纤纤身子微颤,摇头间手抓得更紧了,她还待开口,已有神捕营的人上前将她强制拉开。
台上天玑王子又悠悠道:“付大人,还请快些决断吧。”
付朗尘的背影僵化住一般,与孟蝉久久对视着。
慕容钰的心忽然跳得很快,他再也忍耐不住,几步上前:“付朗尘,你想清楚,那可是孟蝉啊!”
还好叶书来手疾眼快,将他死死一拉,压低声音喝道:“别再添乱了!”
慕容钰心性单纯,只道不过一场论礼罢了,输了便输了,但他却不知,这已经不仅仅是关乎一场论礼的成败了。
付朗尘被逼至悬崖边上,退无可退,自己摔得粉身碎骨不可怕,怕就怕在,他肩上还担着一个国家。
叶书来比谁都清楚,纵是付朗尘有三寸不烂之舌,此刻也毫无用武之地,怎样都是无解,多说多错,越说越糟糕,只会适得其反。
冷风肃杀,满场静寂,付朗尘目光缓缓扫过众人,那些东穆子民满心期许地望着他,天玑王子也适时轻笑一句:“礼法二字,全在付大人一念之间。”
付朗尘藏在袖中的手骤然握紧,最后望了一眼孟蝉后,侧过身去,喉头滚动,一字一句,在场中铿锵响起:“下官依旧是那句话,祖宗之法不可废,千秋之礼不可乱,此乃东穆基石也。”
被神捕营拉住的苗纤纤,忽地激烈挣扎起来,慕容钰更是陡然瞪大双眼:“不,付朗尘你不能!”
但那个声音还是坚定地在场中响起,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入众人耳中:“台下二人,论律当诛,押下去,打入死牢!”
轰然一声,慕容钰脑中似有广厦倾塌,他几乎是一声嘶喊:“付朗尘,你疯了吗?”
天玑王子仰首大笑,拊掌道:“付大人真不打算求情吗?”
付朗尘面不改色,犹如一块冷硬巨石,唇齿轻吐:“国法面前无私恩,纵是天子犯法,也与庶民同罪。”
他一挥手,语调陡然拔高:“押下去!”
“不!”慕容钰血红了眼,想扑上前,却被叶书来死死拦住,他也顾不得仪态,只紧紧钳住慕容钰的腰,低头在他耳边疾声道:“你如果真想害死他们就冲上去!”
他喘息着:“先听付七的,等这天玑使团走了再说!”
慕容钰胸膛起伏,隔着叶书来,眼睁睁看着侍卫队围住孟蝉,就要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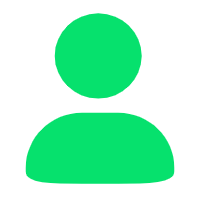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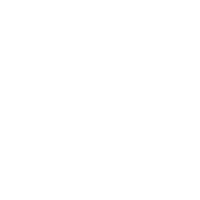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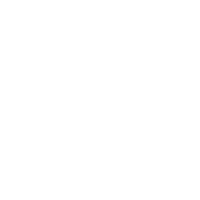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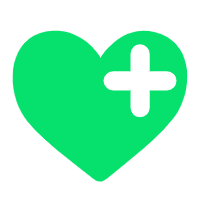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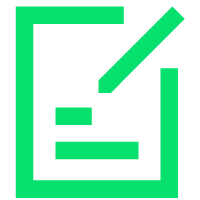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哦,快来首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