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梦醒时分
说着,她竟当着众人之面,一头撞在了柱上,当场血崩身亡,袁沁芳哭晕在地。
这下死无对证了,而先前买凶之事也的确都是染儿一人接头,袁沁芳并未真正出面过,除了往牢中送毒酒外,也只有慕容钰一人的证词。那牢里的狱卒并未瞧见袁沁芳的脸,只收了染儿的钱,染儿咬死都是她一人主谋,小姐并不知情,也不在场。即便余欢出来指认,也只能证明信是交给了染儿,没办法证明袁沁芳参与了此事。
而那封模仿了付朗尘笔迹的信,也在牢中被烧得干干净净,总而言之,人证物证俱不在,除了慕容钰的“一面之词”外,谁也没法定袁沁芳的罪。事情演变到最后,成了一场“恶仆”风波,就连太子也赶来替袁沁芳说情,信她蒙在鼓里,只是管束不力,让婢女接连犯下祸事。
袁沁芳更是在付朗尘面前痛哭流涕,自请逐出付府,愿替婢女赎罪,遁入空门,从此再不问世事。
在太子的主张下,她入得青云观,拜在了紫薇道君的师姐——元芜师太座下,改法号为“寂芳”,留在山上,对青灯拂尘,日日替亡魂超度。
这事便这样告一段落,只是众人没有想到,时隔数月后,在今夜这场家宴上,又会见到袁沁芳。
她随元芜师太前来,坐在右侧下方,埋首不语,身形清减许多,一派真正出家人的模样。
觥筹交错间,慕容钰却是第一个沉不住气,腾地站起,打断了满堂歌舞。
“恕我眼拙,这酒肉声色之宴上,怎么还坐了两位道姑呢?”
他昂首走出,停在袁沁芳跟前,目光灼灼:“这位小师父很眼熟啊,现下是该叫你沁芳小姐呢,还是寂芳道姑?又或是……杀人凶手?”
此话一出,满堂皆惊,一同来赴宴的李麻子、周蛮牛、孙胖胖三人更是低声喊道:“阿钰,快回来!”
首座之上,太子脸色一沉,旁边的付朗尘却自斟自饮,俊颜酡红,目光迷离,对场中发生的一切视若无睹,心神不知游到哪里去了。
对面的叶书来缓缓展开折扇,静观这一幕,他旁边一桌坐着的正是神捕营的人,除了老大顾督公外,那立了功的黎捕头和苗纤纤也在其间。
苗纤纤本来自见到袁沁芳的第一眼起,就一直难掩怒气,此刻见慕容钰出来闹腾,觉得大快人心,不由得拍桌解气。
那头慕容钰还在咄咄逼人着:“问你话呢?哑巴啦?”
袁沁芳着一身素衣,灰扑扑地埋着头,一声也不吭。
慕容钰还要上前再问,首座上的太子终是忍不住,一拍案几:“是我请她们来的,慕容退下,不得无礼。”
慕容钰俊美的脸庞一抬,眸含讽意:“敢问太子哥哥,以什么名义请这两位姑子来的?”
太子眸光一沉:“青云观为皇家道观,我与元芜师太也乃旧交,此次为付府代办家宴,邀她与徒儿一同来赴宴,还需要问过你慕容小侯爷吗?”
说着,她竟当着众人之面,一头撞在了柱上,当场血崩身亡,袁沁芳哭晕在地。
这下死无对证了,而先前买凶之事也的确都是染儿一人接头,袁沁芳并未真正出面过,除了往牢中送毒酒外,也只有慕容钰一人的证词。那牢里的狱卒并未瞧见袁沁芳的脸,只收了染儿的钱,染儿咬死都是她一人主谋,小姐并不知情,也不在场。即便余欢出来指认,也只能证明信是交给了染儿,没办法证明袁沁芳参与了此事。
而那封模仿了付朗尘笔迹的信,也在牢中被烧得干干净净,总而言之,人证物证俱不在,除了慕容钰的“一面之词”外,谁也没法定袁沁芳的罪。事情演变到最后,成了一场“恶仆”风波,就连太子也赶来替袁沁芳说情,信她蒙在鼓里,只是管束不力,让婢女接连犯下祸事。
袁沁芳更是在付朗尘面前痛哭流涕,自请逐出付府,愿替婢女赎罪,遁入空门,从此再不问世事。
在太子的主张下,她入得青云观,拜在了紫薇道君的师姐——元芜师太座下,改法号为“寂芳”,留在山上,对青灯拂尘,日日替亡魂超度。
这事便这样告一段落,只是众人没有想到,时隔数月后,在今夜这场家宴上,又会见到袁沁芳。
她随元芜师太前来,坐在右侧下方,埋首不语,身形清减许多,一派真正出家人的模样。
觥筹交错间,慕容钰却是第一个沉不住气,腾地站起,打断了满堂歌舞。
“恕我眼拙,这酒肉声色之宴上,怎么还坐了两位道姑呢?”
他昂首走出,停在袁沁芳跟前,目光灼灼:“这位小师父很眼熟啊,现下是该叫你沁芳小姐呢,还是寂芳道姑?又或是……杀人凶手?”
此话一出,满堂皆惊,一同来赴宴的李麻子、周蛮牛、孙胖胖三人更是低声喊道:“阿钰,快回来!”
首座之上,太子脸色一沉,旁边的付朗尘却自斟自饮,俊颜酡红,目光迷离,对场中发生的一切视若无睹,心神不知游到哪里去了。
对面的叶书来缓缓展开折扇,静观这一幕,他旁边一桌坐着的正是神捕营的人,除了老大顾督公外,那立了功的黎捕头和苗纤纤也在其间。
苗纤纤本来自见到袁沁芳的第一眼起,就一直难掩怒气,此刻见慕容钰出来闹腾,觉得大快人心,不由得拍桌解气。
那头慕容钰还在咄咄逼人着:“问你话呢?哑巴啦?”
袁沁芳着一身素衣,灰扑扑地埋着头,一声也不吭。
慕容钰还要上前再问,首座上的太子终是忍不住,一拍案几:“是我请她们来的,慕容退下,不得无礼。”
慕容钰俊美的脸庞一抬,眸含讽意:“敢问太子哥哥,以什么名义请这两位姑子来的?”
太子眸光一沉:“青云观为皇家道观,我与元芜师太也乃旧交,此次为付府代办家宴,邀她与徒儿一同来赴宴,还需要问过你慕容小侯爷吗?”
这话有些愠怒了,孙胖胖三人组吓得就想站出来,把慕容钰拖回去,慕容钰却已先开口道:“自然不必问过我,但家宴家宴,既然是付府的家宴,为何不问问首座上那位付大人呢?”
太子怒不可遏:“你!”
说起来太子也是煞费苦心,抱着一片好意,他曾痛失挚爱,便希望天下有情人都能有个好结果,尤其是付朗尘和袁沁芳这一对,他总觉得遗憾满满,自己也有些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以总怀着撮合之意,尤其在看到付朗尘为情所伤,萎靡不振后,他更是希望有人能将他拉出泥潭,重获新生。
而在他心中,那个人,除袁沁芳别无他人了。
这就是他代办这场家宴最重要的目的,可惜太子并不知,他实在是“一厢情愿”,自我揣度过头了。
当下付朗尘依旧懒懒倚在座上,对场中局面不闻不问,只如一摊烂泥般,叶书来不由得一声叹息,摇头担忧。
而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元芜师太,终究是被慕容钰挑衅的态度惹恼,拂尘一扬,冷若冰霜道:“前尘往事,已是过眼烟云,世间早已无袁氏沁芳,只有一法号为寂芳的清心修行人,施主又何必处处刁难,执着于过往?”
慕容钰听得冷笑不止。
“清心修行人?”他忽地伸出手,出其不意地将袁沁芳头上的纱帽一把掀了,那满头青丝瞬间抖落下来。袁沁芳终是变了脸色,慌乱不已地就想拾起纱帽再戴上,却被慕容钰一脚踩住。
他笑意狠绝:“好一个寂芳道姑,你告诉我换身衣裳,戴个帽子,拿柄拂尘,就变成了修行人寂芳吗?”
他俯身凑近浑身哆嗦的袁沁芳:“那干吗还要带发修行?既然诚心悔过,再不入红尘,何不把这一头烦恼丝给绞了,做个真正清心寡欲的出家人呢!”
袁沁芳煞白了脸,颤抖着声音解释道:“佛道有别,寂芳在青云观修行,本就无须落发……”
慕容钰哈哈大笑:“难怪你去了道观,没去庵堂,原是打着这般主意,我看你根本就没舍下这红尘吧!”
他眸光一厉,又凑近袁沁芳一步,揪住她一缕长发:“你既下不了手,不如我来帮个忙,好歹夫妻一场,我乐意之至!”说着,竟是手下用力,扯得袁沁芳头皮一痛。
旁边的元芜师太忍无可忍,倏然站起,拂尘正要出手之际,首座上的太子已重重一拍案几:“够了,慕容钰,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去?!”
这一下是真的动怒了,慕容钰冷笑着松了手,挑眉正要开口时,太子旁边的付朗尘醉醺醺地睁开了眼,俊秀的脸庞似染胭脂般,歪歪扭扭地拂袖指向堂下,笑意迷蒙:“敢问、敢问太子殿下,小侯爷说的……哪里错了?”
这是他今日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却让满座皆惊,尤其是太子殿下与堂下眼中含泪的袁沁芳。
付朗尘却自顾自地打了个酒嗝,睨了袁沁芳一眼,随手从怀中抛出一物:“既要斩断过往,我这儿倒有把好匕首,不若借给小侯爷用用。”
匕首划过半空中,叫慕容钰接了个正着,他微微一怔,紧接着却是扬眉笑开:“好东西好东西,付大人的东西就是雅致精巧,可惜本侯用不惯,因为本侯——嫌脏!”
最后两个字吐出时,眸光也瞬间冷厉下来,付朗尘却面不改色,反而仰首大笑,以筷击桌,状似疯癫:“不错,甚妙,小侯爷说得一点也没错,何止是这把匕首脏啊,眼睛、耳朵、嘴巴,哪一处不脏呢?”
他头上的发髻散落一半,半遮半掩住那张酡红俊颜,清逸至极的气质生生透出几分妖冶来。
“一双识人不明的眼,一对屡遭蒙蔽的耳,一张出口伤人的嘴,脏透了,里里外外,真是脏透了……”
颠三倒四中,座下的叶书来终于再也听不下去了,起身道:“付七,太子表兄还在场呢,你收敛点,即便是家宴,你也不可这般放肆啊……”
付朗尘微眯了眸打断:“放四?没有啊,谁把四放走了?怎么不把五六七八九一起放了呢?”
“够了!”太子终将全部耐心耗尽,痛心不已地拂袖站起,“罢了罢了,这乌七八糟的一团死结,本宫是再也不想管了!”
满堂噤若寒蝉,眼见太子便要离席而去时,神捕营的顾督公悠悠开口道:“老夫忽然想到一件趣事,不若说与在座各位听听,太子殿下也稍后再走,难得家宴一场,何至于弄得不欢而散?”
他坐镇神捕营多年,周身气势浑然天成,这么一出来打圆场,谁也不自觉地给上面子,洗耳恭听起来,连慕容钰也回了座,喝着闷酒不再闹腾。
这顾督公说的趣事,其实也不过发生在东山百里外,那里有几座村落,近来常常发生诡异之事,鸡鸭横死,血流满地,屋顶三天两头出现烧灼痕迹,更有人撞见月下两团黑影,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疾速扑入山林之中。村民们害怕,连进山狩猎都不敢了,只好找上神捕营,希望能捉拿住那两个“猛兽”,还他们安生。
顾督公娓娓道来,众人不觉听入了迷,连发髻散乱的付朗尘也顿住了酒杯,长睫微颤,侧耳静静听着。
“诸位定是猜不到,神捕营的弟兄们守了好几夜,最后瞧见了什么?那可并非何种山野猛兽,乃是两个奇形怪状的人啊!不,亦称不上人,一个满头蓝发,生有蝉翼,周身寒气逼人;一个满头赤发,踩在屋顶上,便留下一个烧灼印记,骇人不已……”
顾督公摇头叹道:“这般怪物,不该请神捕营去捉拿,该叫上青云观的高人去布阵才对,可不就是山中生妖孽,精怪化人形吗?”他说着,看向旁边,戏谑道,“元芜师太,依你看,这是……”
话还未说完,对面的慕容钰霍然站起,浑身抖得不成样子,对着顾督公激动道:“什么蓝发蝉翼,眼睛呢,眼睛也是蓝色的吗?是不是像结了一层冰一样?”
顾督公一愣,略微吃惊道:“正是如此形貌,小侯爷如何得知?”
慕容钰手一抖,径直打翻了桌上杯盏,他几步跨出,不顾众人惊诧目光,几乎是踉跄跌到那顾督公跟前:“快,有画像吗?快拿画像给我看一眼!”
饶是顾督公再好的定性,也有些措手不及:“画……画像,都尽数贴在了周边村落里,不过还有一张收在了神捕营中……”
“神捕营,神捕营……”慕容钰像疯了一般,跌跌撞撞地就朝门外奔去,连太子在他身后连唤数声都没听到。满堂哗然间,首座上的付朗尘也一下蹿起,双眸大亮,发髻散落地就跃至堂下,什么礼数都顾不上,紧追那慕容钰而去。
一片惊呼中,叶书来与苗纤纤对视一眼,福至心灵般,也猛地起身,同时离席奔出了门,这一连串动静把太子看得是目瞪口呆,嘴都合不上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一个两个的,都疯了不成?”
2.山神之魂觉醒
石洞昏暗无光,一团冰蓝身影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着,又一次陷入了梦魇之中。
火势熊熊逼近,将他们彻底包围住,绝望在牢中蔓延开去,没有人会来救他们,那个曾说要一生一世照顾他们的人,却下了最残忍的狠手,那些至死都不愿相信的东西,在无情的大火中被彻底揭开,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自欺欺人是真的……
“不要,不要……”
冰蓝色的眼睛陡然睁开,额上冷汗涔涔,踏入洞穴的那袭红衣正听到这句,赶紧奔上前,将那团冰蓝身影搂入怀中。
“姐姐,你又做噩梦了吗?”
他手臂强劲有力,身躯颀长,红发下的面容俊逸邪气,充满凛冽野性,是个真真正正的男人了,再非从前那个不谙世事的小不点。
冰蓝色的眼却看向他唇边,抚去那一抹血丝,颤声道:“你、你又去山下了?”
男子一惊,这才发现用食完后的嘴角未擦干净,他手忙脚乱地抬手就去抹掉,却到底抵不住那双冰蓝眸子投来的目光,低下头,闷闷承认道:
“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化,要消耗的体力实在太大了,没有东西吃,怎么活下去呢?”
冰蓝色的双眸一暗,许久,才轻轻道:“那你……跟他们动手了吗?”
男子头一抬,赶紧摆手:“没有没有,我听你的,他们朝我放箭,我就跑,头都没回一下呢……”
他说着声音又沉了下去:“倒是他们,我没伤过他们一根手指头,他们的箭却射中我的手臂了,流了很多血,很痛……”
冰蓝色的双眸一惊,纤秀的手关切地探上前:“又受伤了吗?在哪里?我看看……”
“小伤,在溪边洗干净了。”男子微微侧过身,垂下眼睫,昏暗的石洞里,一股不甘的恨意又涌上心间,“可是,姐姐,凭什么?”
他有力的臂膀狠狠一捶地,咬牙切齿道:“凭什么我们就要这样东躲西藏,被人当作怪物驱逐追杀,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凭什么那些人就能对我们喊打喊杀,任意伤害我们?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冰蓝色的身影连忙将男子抱住,贴近他灼热的胸膛,不住安抚道:“别恨,别激动,到时身体又会难受,你现在还不能控制……”
男子被那冰寒之气冷却心头翻滚热血,却仍不甘地咬牙道:“都怪那个人,都怪他,我恨他,恨不能将他烧成灰烬……”
那日烈火滔天的牢里,付朗尘也许永远也想不到,孟蝉与初一经历了些什么。
当他们被火舌包围住,痛楚、不甘、绝望等情绪各番涌来时,初一身上忽然水光大作,脖颈间渗出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子,幻化出清寒水雾,将他与孟蝉紧紧包裹住,避开熊熊烈火。
那珠子,正是上元节那夜,水泽星君送给初一的碧水珠,蕴藏了几近一条河的水量。
在碧水珠的包裹下,孟蝉与初一虽未受烈火焚身,但却在极度的绝望刺激下,身体同时发生了骇人变化!
大火之中,孟蝉仰头发狂,双瞳刹那变色,长发尽蓝,背上更是陡然生出一对蝉翼,劲风狂卷。
初一则由懵懂稚童一下抽丝剥茧长大般,骨骼咔嚓作响,在撕心裂肺的痛楚中,瞬间化作一个身形高大的赤发男子。
这变化太过悚然骇人,孟蝉看着自己的身体大受刺激,仰头长啸,展开双翼,带着初一冲破牢房顶部,飞入了夜空之中……
无法言说最初那段流落的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孟蝉蹲在溪边,浑身剧颤,怎么也无法接受水中自己的模样,她疯狂拍打着水面,嘶声凄厉,甚至想要生生将背上一对蝉翼撕裂下来!
还好初一紧紧按住她的手脚,抱紧她,在山中的猎人闻声赶来前,带她躲进了密林之中。
从此他们便过起了“野人”般的生活,东躲西藏,遮掩度日,还要忍受身体时不时袭来的痛苦。
初一发作时,体内便如岩浆流淌,从头到脚赤焰灼灼,似要将他燃成灰烬,炸裂一般,痛不欲生。
孟蝉发作时,浑身会从那对蝉翼开始,结上一层薄薄的冰霜,寒气钻心入骨,让她彻夜难寐。
他们在山里忍受着这冰火两重天的折磨,只能相互依偎支撑,但更多的痛苦,是从心底源源不断升起的。
那些对身体的惶恐与抗拒,那些梦魇里的不甘与恨意,那些东躲西藏的狼狈与不堪,日日夜夜地折磨着他们,让他们如坠炼狱,不知何时才能挣脱看到尽头。
也许那一天很快会来临,也许永远也不会来临,他们只能隐匿在荒郊野岭里,做着暗无天日的怪物,舔舐着无人知晓的伤口,了却残生……
宴秋山,月光如水,湖面波光粼粼,天地静谧。
山间摆着一副棋盘,两道谪仙般的身影正在月下对弈。
风掠山岚,终究是水泽星君先沉不住气,抬头叹道:“喂,我说竹君,咱们这盘棋,真要下到年年岁岁,天荒地老去吗?”
他对面的徐清宴一袭青衫,眉目沉静如水:“不是你提议静心下棋吗,现在又按捺不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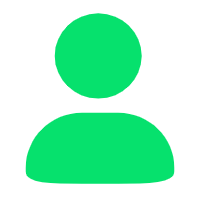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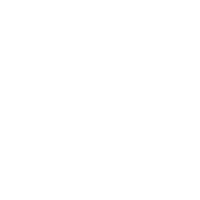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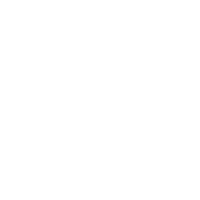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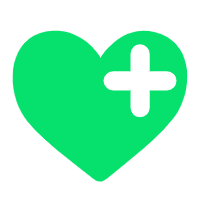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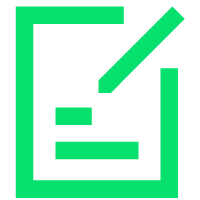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哦,快来首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