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岁谢莲
他们的关系奇怪得让谢容忍不住去探究,直到有一次,他看见洛芷在后院洗衣服……
丰澜谷终年飘雪,她的一双手冻得通红。他忍不住就想跃下树,远处却忽然跑来一群姬人,领头的将一个木匣狠狠掷在她面前,横眉厉喝:“洛芷,从你房里搜出来的,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那木匣被摔在地上,里面的几捆丝线散落在雪中。洛芷一下就慌了,低头去捡:“我的蚕丝……”
她还来不及触碰到,已被一脚踹翻在地。风雪呼啸中,她们将她团团围住:“小偷,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蚕丝线,一定是从采办姑姑那里偷的!”
七嘴八舌的声讨里,有人去撕扯她的衣袖,还有人拿起浣衣棍敲打她一双“贼手”,不多时她便一身狼狈,手臂上遍布红痕。
漫天风雪中,她不住地哀求着:“不,不是的,我没有偷东西,这是我从采办姑姑那儿换来的……”
树上的谢容捏紧双拳,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洛芷是如何辛苦换得这蚕丝的。
丰澜谷每月都有姑姑负责采办,按位分发给谷中姬人。好东西当然轮不到洛芷,她每次都只能拿到一份最低等的胭脂,就这,洛芷还藏得跟个宝贝似的。
哪会有女子不爱红妆呢?谢容曾亲眼看见洛芷坐在铜镜前,小心翼翼地蘸起一点胭脂,抹在嘴唇上,对镜一笑,苍白的一张脸瞬间有了点颜色。
但她很快就将胭脂收好,那时谢容还以为是她舍不得用,直到他看见她拿着胭脂去采办姑姑那儿换蚕丝,是的,上好的蚕丝,每次只能换一点,但她显然已经换过很多次了,积少成多,竟也不知不觉地让她攒够了。
晚上谢容问她,她在烛火摇曳下,抱紧木匣浅笑:“公子夜间多梦,我想用蚕丝给他做个香囊,内置药草,有安神之效……”
那一刻,夜风飒飒。谢容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他只是忽然羡慕起一个人来。
那个人,自然是洛雪衣。
如今藏于树间,眼见洛芷被无故冤枉,谢容再顾不上许多,就想跃下树来替她解难,却是余光一瞥,竟看见长廊尽头,一道身影迎风而立,白发飞扬,正是洛雪衣。
他依旧冷着一张冰块脸,看着眼前的一切无悲无喜,谢容本要伸出的脚蓦地就顿住了,他在等。
他想,哪怕这个男人不站出来,而只是为洛芷的遭遇稍微皱一下眉,那洛芷也是值得的。但没有,什么也没有。
直到采办姑姑赶来,还了洛芷清白,让一场闹剧匆匆结束,他仍旧站在长廊上,一动也没有动过。
姬人们讪讪散去,廊下的那身雪衣也拂袖而去,来得寂寂,去也悄无声息,仿若浩浩天地间的一片雪。
树上的谢容抿紧唇,凝视他远去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而树下的洛芷却踉跄起身,不顾满身伤痕,将散落在地的蚕丝一一捡回,衣裳凌乱地坐在雪地里,抱着木匣松了口气。
他们的关系奇怪得让谢容忍不住去探究,直到有一次,他看见洛芷在后院洗衣服……
丰澜谷终年飘雪,她的一双手冻得通红。他忍不住就想跃下树,远处却忽然跑来一群姬人,领头的将一个木匣狠狠掷在她面前,横眉厉喝:“洛芷,从你房里搜出来的,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那木匣被摔在地上,里面的几捆丝线散落在雪中。洛芷一下就慌了,低头去捡:“我的蚕丝……”
她还来不及触碰到,已被一脚踹翻在地。风雪呼啸中,她们将她团团围住:“小偷,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蚕丝线,一定是从采办姑姑那里偷的!”
七嘴八舌的声讨里,有人去撕扯她的衣袖,还有人拿起浣衣棍敲打她一双“贼手”,不多时她便一身狼狈,手臂上遍布红痕。
漫天风雪中,她不住地哀求着:“不,不是的,我没有偷东西,这是我从采办姑姑那儿换来的……”
树上的谢容捏紧双拳,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洛芷是如何辛苦换得这蚕丝的。
丰澜谷每月都有姑姑负责采办,按位分发给谷中姬人。好东西当然轮不到洛芷,她每次都只能拿到一份最低等的胭脂,就这,洛芷还藏得跟个宝贝似的。
哪会有女子不爱红妆呢?谢容曾亲眼看见洛芷坐在铜镜前,小心翼翼地蘸起一点胭脂,抹在嘴唇上,对镜一笑,苍白的一张脸瞬间有了点颜色。
但她很快就将胭脂收好,那时谢容还以为是她舍不得用,直到他看见她拿着胭脂去采办姑姑那儿换蚕丝,是的,上好的蚕丝,每次只能换一点,但她显然已经换过很多次了,积少成多,竟也不知不觉地让她攒够了。
晚上谢容问她,她在烛火摇曳下,抱紧木匣浅笑:“公子夜间多梦,我想用蚕丝给他做个香囊,内置药草,有安神之效……”
那一刻,夜风飒飒。谢容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他只是忽然羡慕起一个人来。
那个人,自然是洛雪衣。
如今藏于树间,眼见洛芷被无故冤枉,谢容再顾不上许多,就想跃下树来替她解难,却是余光一瞥,竟看见长廊尽头,一道身影迎风而立,白发飞扬,正是洛雪衣。
他依旧冷着一张冰块脸,看着眼前的一切无悲无喜,谢容本要伸出的脚蓦地就顿住了,他在等。
他想,哪怕这个男人不站出来,而只是为洛芷的遭遇稍微皱一下眉,那洛芷也是值得的。但没有,什么也没有。
直到采办姑姑赶来,还了洛芷清白,让一场闹剧匆匆结束,他仍旧站在长廊上,一动也没有动过。
姬人们讪讪散去,廊下的那身雪衣也拂袖而去,来得寂寂,去也悄无声息,仿若浩浩天地间的一片雪。
树上的谢容抿紧唇,凝视他远去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而树下的洛芷却踉跄起身,不顾满身伤痕,将散落在地的蚕丝一一捡回,衣裳凌乱地坐在雪地里,抱着木匣松了口气。
那一瞬,谢容的鼻头忽然泛酸,他遥望远山长空,只觉得这样的姑娘不该有此遭遇,更不该执着于那个铁石心肠的人。
他霎时萌发了一个念头。
在又一次为洛雪衣施针后,洛芷跪在大殿中,鼓足勇气送出了那个她赶制了好几夜的香囊。
但洛雪衣只是随手接过,拂袖一抛,将香囊直接扔进了一旁的火炉里,暗处的谢容差点惊呼出声。
“夜间多梦与你有何干系?我不需要这种小玩意儿,你做来也没用,何苦白费心思?”
帘幔飞扬,殿里响起洛雪衣冷冷的声音。跪在地上的洛芷浑身颤抖着,眼睁睁地看着火舌一点点吞噬掉香囊。她不敢出声也不敢动弹,只是过了许久,才低下头去,有泪珠坠落殿面:“是,公子。”
那一瞬,暗处的谢容屏住呼吸,极力抑制住翻滚的情绪,脑海中的那个念头愈发强烈,他一刻也不想再等下去了。
两天后的一个夜里,趁守卫松懈,他终于行动,潜入洛芷房中,出其不意地点昏她,将她掳走。
洛芷醒来时已身在苍鹰堡,一睁眼便看到谢容红袍烈烈,捧着一怀的莲花站在她床前。
“好看吗?这是我们苍鹰堡的红莲,天下独绝,这个季节开得最好了。”
起初很长一段时间,洛芷都被谢容弄得哭笑不得,无计可施。
同苍鹰堡的亦正亦邪一般,他也是个很神奇的存在,身上既有孩子气的一面,又有霸道不讲理的一面。
他不准洛芷离开,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在“解救”她,以报她的救命之恩。洛芷如何说也说不通,还被他成天拉着去看红莲。
红莲开在山崖下面的一大片云池里,每到黄昏时分,晚风轻拂,水面泛起涟漪,云雾间红莲摇曳,那样的场景美不胜收。
谢容就像个迫不及待要和人分享的孩童一样,将自己的“秘密基地”一五一十地展示给洛芷看,还为洛芷跃下云池,捧出一怀又一怀的红莲。
湿漉漉的长发贴在背上,他与她在夕阳中四目相对,一字一句说得极其认真:“因为所有人都对你不好,我看着不爽,就特别想对你好,想和所有人作对。”
那时洛芷坐在崖边,听得真切。夕阳中谢容的一张脸水光潋滟,她禁不住就想伸出手为他擦拭,但到底停在了半空。
她低下头,长睫微颤,声音轻不可闻,她说:“可是哥哥给了我姓名,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一个家……我是不可能离开他的。”
是的,哥哥,洛芷告诉谢容,她是个弃婴,是洛雪衣将她捡回丰澜谷,一手带大的,她一直叫他“哥哥”。直到洛雪衣的母亲灵宫主去世,他便再也不许她叫他了,还要将她赶出谷。
态度的陡变令她百思不得其解,多年来一个拼命往外推,一个却怎么也不肯走,因身份不再,她在谷中备受欺凌,可他从来都不管不问。
但不要紧,她想,哥哥一定是有苦衷的。
“他病得很厉害,不过二十有六,已经半白了头,我们曾说过一辈子不分离,也许他怕撑不到那一天,所以才会不停地赶我走……”
只要一谈到洛雪衣,洛芷便会捂住脸,潸然泪下。
谢容与她并肩坐在崖边,共沐夕阳,看飞鸟相还。见她如此模样,又是心疼又是愤愤,抱着一怀红莲,终是忍不住开口道:“生病就很惨吗?那我也身患隐疾啊,不如和你家哥哥比比,看谁病得厉害些?”
果然,话一出,洛芷顿时止了泣声,愕然抬头望向他。
谢容得意扬扬,眉宇间却又有些难以言明的情绪:“你道大家为何都称我一声‘六少’?其实我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只不过尚在襁褓中就夭折了。我虽是侥幸活下来,却也活得不易,每隔数月心疾便会发作一次,届时燥热难安,唯有云池莲水方能平息一二,所以一年之中,我好死不死总得在那云池里泡掉一层皮。这下你说说,到底是你哥哥惨还是我更惨?”
山风掠崖,洛芷听得愣住了,盯着谢容久久不放。谢容被她盯得浑身不自在,还没等她开口,便一下站起,红袍一甩:“当然是你哥哥惨了!”
他哼哼道:“少用那种怜悯的目光看着我,我方才都是骗你的,我才没那么倒霉呢,我堂堂红莲六少,岂是你那病秧子哥哥能比的?!”
说完,他径自跃入云池,掀起水花四溅,还抓住崖边洛芷的脚踝,将她一把拖入池中,嬉笑闹腾起来:“总之你不许走,进了苍鹰堡就别想再出去!”
洛芷在池中尖叫躲闪,夕阳笼罩着两人的身影,笑声飞过长空,一瞬间仿佛无忧又无虑,只是衣袂翩跹间,洛芷眼底始终藏着一抹化不开的忧愁。
在得知丰澜谷三千姬人倾巢出动时,洛芷终于再也坐不住了:“哥哥一定在找我……”
她说着就想冲出屋,却被谢容拦在了门口。外头月色迷蒙,他这些日子天天跑来找她,缠着她也绣个香囊给他,如今香囊才做了一半。他长眉一扬,又露出了蛮横本性:“不准走,我说不准走就不准走!”
洛芷又慌又急,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却在这时,谢容眉头一蹙,身体如遭电击般剧颤起来,一下按住心口,痛苦万分。
“六少!”
苍鹰堡的人围了上来,谢容却推开他们,踉跄着奔入月色中。“扑通”一声,他跳进了山崖下的云池里,水花四溅,红光大作。
追出来的洛芷停在崖边,望着池中狂躁难耐的谢容,脸色大变。她蓦然想起他曾对她说过的话:“我虽是侥幸活下,却也活得不易,每隔数月心疾便会发作一次,届时燥热难安,唯有云池莲水方能平息一二……”
原来,原来他不是在骗她,他真的身患隐疾!
“谢容!”
洛芷在崖边唤他,手都在颤抖。夜风拂过她的衣袂发梢,这是个多么好的机会,她正好可以趁乱离开,以后再想走就难了……
可是……看着池中痛苦的谢容,听着他的声声狂啸。洛芷瘫软在崖边,摸向怀中的银针,指尖颤动,满脸挣扎。
究竟是留,还是走?
红莲如血,云雾缥缈。
谢容在池里泡了整整二十五天,除了每日来送饭的侍女外,还有个人一直在岸边衣不解带地守着他,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洛芷。
她精通医术,每日下池为谢容贴身施针,缓解他的痛苦。谢容偶有清醒之时,长睫微颤间,望着为他忙活的洛芷,眼眸漆黑,不知在想些什么。
一日施针,两人贴得很近,他蓦然伸出手,水花四溅,竟一下搂住了洛芷的腰,吓得洛芷手一颤,一根银针差点扎偏。
“你为什么没走?”
不顾洛芷的尖叫,他定定地望着她,赤裸的上半身精壮有力,将她牢牢地圈在怀中。
洛芷拼命挣扎着,脸颊绯红,不敢看他,只将目光落在别处:“你先放开我,快放开我……”
湿漉漉的长发交缠着,谢容呼吸急促。只听风过莲池,他不知灼热地盯了洛芷多久,一个不防被洛芷推开。她赶紧逃也似的上了岸,他却在池中发愣,见她在岸上面红耳赤,狡黠一笑:“我知道了。”
他站在水里,十足的大言不惭:“因为我太好了,你情不自禁喜欢上了我,对不对?”
洛芷正在岸边整理湿透的衣裳,闻言脸一红,一口啐去:“胡说什么,医者父母心,我不过是谨遵医德罢了。”
“哦?”谢容拖长了音,两手一摊,“那我可真荣幸,被你一救再救,你的‘父母心’未必全用在我身上了?”
岸上的洛芷又羞又窘,却也被他逗笑了,捧起池水向他泼去:“呸,臭不要脸的。”
两人一阵笑闹,风过四野。不觉间斜阳升起,洛芷也渐渐累了,靠在一块石头上睡去。
谢容就那样望着她,周身都染了金边,眸含笑意,只觉天地间无比安静,他胸膛里跳动的那颗心都变得柔软起来。
夜幕降临,月光倾洒。谢容裸着上半身,湿漉漉地涉过莲池,悄无声息地上了岸。
他扯过岸边自己的红袍,轻轻盖在了洛芷身上。月下洛芷睡得正香,清丽的眉目比平时更添几分柔美。他不知端详了多久,终是心痒难耐,俯身吻上了她的额头。
有细碎的呢喃溢出唇齿,他说:“好姑娘,不管你现在喜不喜欢我,将来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喜欢上我的,我等着……”
那大抵是他此生用过最温柔的语气,就在这夜风轻拂的一刻,天知、地知、月知、莲知,唯她不知。
谢容一共在池里多赖了十天,在第十一天,终于被洛芷瞧出。她生气地掉头就走,谢容急忙跃上岸,裹了红袍追上去,一把扣住她的手腕。
“阿芷,别走!”
洛芷不理他,仍是要走。几番纠缠间,他却忽然开口:“你想救洛雪衣吗?”
洛芷一下愣住了,抬头,长睫微颤,只对上谢容深不见底的一双眸。
“你听过五色莲心吗?”
世上有个词叫“乘人之危”,从前谢容从不觉得自己会做这种事,但没想到有朝一日,他居然真的开了口,还是以那种最蛮横的无赖姿态。
“一物换一物,我要你嫁给我,做我苍鹰堡的少夫人,你别无选择,天大地大只能和我在一起!”
他其实刚说完就后悔了,他不想这么粗暴的,这可是他最喜欢的姑娘啊。可他万万没想到,洛芷只惊愕了片刻,便下定决心般,迎上他的目光,轻轻点了点头。
“好,你说话算数。”
他至今也忘不了那天自己的感受,他抱起她在池边转圈尖叫,风吹发梢,红袍烈烈,狂喜过后却升起一股浓浓的悲哀—
原来洛雪衣在她心中的分量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足以让她毫不犹豫地抛却自己,只为换得他余生平安喜乐。
他是她的不得求,而她却是他的求不得,世间之事不是一物换一物,而是一物降一物。
这一年,苍鹰堡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当喧嚣褪去后,没有人知道,安静的新房里,一道屏风隔开了两张床—
这也是当初说好的条件之一,谢容已经派人往丰澜谷送药去了,只有当确认洛雪衣服下五色莲心后,洛芷才会同他圆房,成为真正的夫妻。
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最终等来的是洛雪衣的一具尸体。在送药人赶去丰澜谷时,他已与风雪同眠。不偏不倚,他们恰恰晚了一步。
见到洛雪衣的尸体后,洛芷的情绪几乎失控。她哭到昏厥,醒来后一双明眸如蒙水雾,再也看不见了。
而比她更绝望的却是谢容,这世上他比谁都希望洛雪衣好好活着,因为只有他好好活着,才能换得他和洛芷的来日方长。
可一切都被打乱了,他还没能等到洛芷慢慢喜欢上自己,他们中间的那道屏风就已经再也撤不去了。
三年转眼而过,洛芷拄着盲杖,去的最多的地方便是阁楼顶层的冰棺前,问他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另一颗五色莲心找到了吗?”
谢容心疼她,对着冰棺前的她又气又急:“洛雪衣一辈子不醒过来,你就打算一辈子不医治眼睛吗?你学这么多年医究竟是为了什么?”
洛芷素衣白裙,额头抵在冰棺上,双手轻抚,是无比眷恋的姿势。不知过了多久,她的声音才像从天边传来:“十岁那年中秋,我第一次为哥哥做月饼,却不小心冲撞了灵宫主,连累哥哥与我一同受罚,他替我挡去了大半鞭笞。我们被关在殿中思过一夜,那时他浑身都是血,我怎么叫他都不醒,我差点以为,以为他……”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医,因为我再也不想看见哥哥受伤了,我采百药、翻古籍、练银针,一切的一切,从来都只是为了哥哥。
“如果哥哥再也醒不过来了,我还要那医术做什么?还要这双眼睛做什么?”
声音在冰室中久久回荡着,谢容胸膛起伏,无数情绪涌上心头,却终是红袍一甩,跑出了阁楼,径直跃入崖下的云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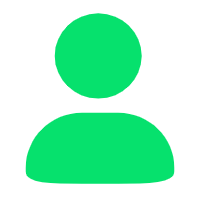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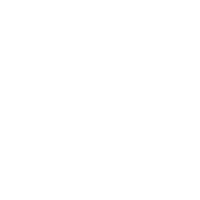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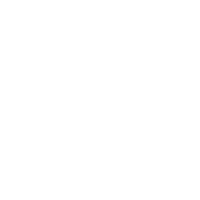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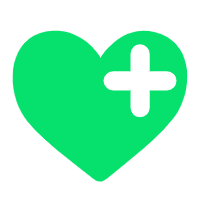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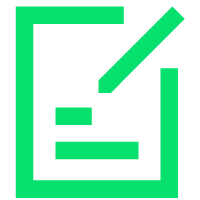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哦,快来首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