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妻子婳
才七八岁的小姑娘,踏着一双漂亮的马靴,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衫子,明眸皓齿,灿烂耀眼得不像话。
那是后来回想起都不可思议的一幕,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几位哥哥,低垂着脑袋,噤若寒蝉,看着那道纤秀的身影将他拉起,为他拍掉身上的灰,冲他一笑—
“好可爱的小兔子啊,我正好属兔,能不能把这个木雕送给我?”
那是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多么神奇,她既没有为他呵斥别人,也没有直指他的狼狈不堪,只是若无其事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却让他觉得,整片天都亮了起来。
漫天的琼花落下,他们四目相对,长风掠过衣袂发梢,他漆黑的瞳孔里映满了她的笑。
相府明珠拒收所有人的礼物,唯独收了霍家一个庶子送的白兔木雕,这件事一度让都城世家们为之哗然。
此后几年,霍仲珍过得无比开心。
凡子常来找他玩,他为她雕出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但雕得最多的还是兔子,那仿佛成了他们之间一份特殊的温暖。
而他的身体也渐渐好转,凡子为他请了大夫调养,他更不用三天两头挨打了。
但所有改变中,最叫他触动的,还是“娇娇”这个绰号。
那是一次春日宴席,霍家子弟俱在场,凡子忽然对他道:“拂浪堤垂柳,娇花鸟续吟,这么好听的名字,以后只许我叫好不好?”
声音不大,但一字一句足以叫在场所有人都听清楚。从此以后,霍家再也没人敢叫他“娇娇”了。
原来不堪忍受的羞辱,忽然变成了丝丝入心的甜蜜。霍仲珍第一次觉得“娇娇”这样的名字,从凡子口中叫出……是那样好听。
他成了她的专属,而她也珍藏在他心底,只是他一人的白兔。
这一年,琼花开得极好,漫天飞舞。他们正式定亲,年轻的相爷召见他,对他说了那样一番话。
“庶子又如何?我凡子衿的妹妹,还不需要牺牲姻缘去铺路,功名利禄我可以去挣,她只要好好笑着就行了。”
身居高位的丞相一拂袖,将目光从窗外月色转到他身上:“而你,会让她一直那样笑,对吗?”
从房里出来后,霍仲珍双手都在颤抖。才十五岁的少年,几乎承受不住那样大的喜悦。
屋外竹影斑驳,等候已久的凡子一步步走向他,走到他跟前时歪着头冲他笑。他再也忍不住,一把将她揽入怀中,脑袋埋在她颈间,许久,竟是哭了。
他说,他想他娘了,如果他娘还在,该有多好……
“没娘的孩子本来就很苦,我也是哥哥一手带大的。不过现在不同了,娇娇,我有哥哥,你有我,我们是一家人了,你说是不是?”
夜风飒飒,凡子轻拍着他的后背,像儿时兄长安抚啼哭的自己一般。霍仲珍重重点头,抱住她的手又紧了紧。
月色迷蒙,窗边的凡子衿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幕。天地间静悄悄的,就在这一夜,这场只有三个人祝福的姻缘,被坚信能够天长地久。
才七八岁的小姑娘,踏着一双漂亮的马靴,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衫子,明眸皓齿,灿烂耀眼得不像话。
那是后来回想起都不可思议的一幕,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几位哥哥,低垂着脑袋,噤若寒蝉,看着那道纤秀的身影将他拉起,为他拍掉身上的灰,冲他一笑—
“好可爱的小兔子啊,我正好属兔,能不能把这个木雕送给我?”
那是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多么神奇,她既没有为他呵斥别人,也没有直指他的狼狈不堪,只是若无其事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却让他觉得,整片天都亮了起来。
漫天的琼花落下,他们四目相对,长风掠过衣袂发梢,他漆黑的瞳孔里映满了她的笑。
相府明珠拒收所有人的礼物,唯独收了霍家一个庶子送的白兔木雕,这件事一度让都城世家们为之哗然。
此后几年,霍仲珍过得无比开心。
凡子常来找他玩,他为她雕出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但雕得最多的还是兔子,那仿佛成了他们之间一份特殊的温暖。
而他的身体也渐渐好转,凡子为他请了大夫调养,他更不用三天两头挨打了。
但所有改变中,最叫他触动的,还是“娇娇”这个绰号。
那是一次春日宴席,霍家子弟俱在场,凡子忽然对他道:“拂浪堤垂柳,娇花鸟续吟,这么好听的名字,以后只许我叫好不好?”
声音不大,但一字一句足以叫在场所有人都听清楚。从此以后,霍家再也没人敢叫他“娇娇”了。
原来不堪忍受的羞辱,忽然变成了丝丝入心的甜蜜。霍仲珍第一次觉得“娇娇”这样的名字,从凡子口中叫出……是那样好听。
他成了她的专属,而她也珍藏在他心底,只是他一人的白兔。
这一年,琼花开得极好,漫天飞舞。他们正式定亲,年轻的相爷召见他,对他说了那样一番话。
“庶子又如何?我凡子衿的妹妹,还不需要牺牲姻缘去铺路,功名利禄我可以去挣,她只要好好笑着就行了。”
身居高位的丞相一拂袖,将目光从窗外月色转到他身上:“而你,会让她一直那样笑,对吗?”
从房里出来后,霍仲珍双手都在颤抖。才十五岁的少年,几乎承受不住那样大的喜悦。
屋外竹影斑驳,等候已久的凡子一步步走向他,走到他跟前时歪着头冲他笑。他再也忍不住,一把将她揽入怀中,脑袋埋在她颈间,许久,竟是哭了。
他说,他想他娘了,如果他娘还在,该有多好……
“没娘的孩子本来就很苦,我也是哥哥一手带大的。不过现在不同了,娇娇,我有哥哥,你有我,我们是一家人了,你说是不是?”
夜风飒飒,凡子轻拍着他的后背,像儿时兄长安抚啼哭的自己一般。霍仲珍重重点头,抱住她的手又紧了紧。
月色迷蒙,窗边的凡子衿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幕。天地间静悄悄的,就在这一夜,这场只有三个人祝福的姻缘,被坚信能够天长地久。
只是时移事易,谁也没有料到,相府的衰败会来得那么快。
凡子衿为相本就孤傲疏狂,定亲一事,又暗中得罪了不少世家权贵,而党派之争愈演愈烈,渐渐的,相府的光景就大不如前了。
而就在这时,相府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凡子不小心从假山上摔了下来,头部受创,一夜之间心智倒退如懵懂幼童。
用外界幸灾乐祸的话来说就是,她傻了,彻彻底底成了个傻子。霍家私下甚至有更难听的话传出,说老天有眼,怎么可能便宜霍仲珍这下贱的庶子,还就是他“克”傻了从前那众星捧月的大小姐!
风言风语里,也不知霍仲珍是听了去,还是见相府日渐式微,总之一番变故后,他已经很少去相府了。
有人说他聪明,有人嗤他薄情,更多的人是嘲笑他一辈子翻不了身。就在这样的纷纷扰扰中,皇城的天终于变了。
婚期前两月,相府垮台,满门被抄,凡子衿获罪入狱,全部亲族贬为庶人。
阴暗潮湿的死牢里,霍仲珍见了凡子衿最后一面。
这个一生骄傲的男人,负手而立,身着囚服也不掩疏狂气质。他目视霍仲珍淡淡道:“旁人怎么说我不管,官场浮沉数十年,我总信自己的眼光,从今天起,我就把妹妹交给你了,请你一定要善待她。”
他工于权谋,一步步爬到丞相之位,双手干净不了,或许从不是个良善臣子,但却一定是世上最好的哥哥。
从牢里出来后,霍仲珍半天没有缓过神来,他靠着城墙一点点滑坐下去。仰望夜空,繁星入眸,有冰凉的泪水流过眼角,苍白无力如命运一般。
承平十二年,凡子嫁入霍府,无嫁妆无排场,甚至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只顶着“奸臣家傻妹”的名头,在霍家人不怀好意的窃笑中,开始了一场望不见头的悲剧。
凡子可以说是众人逼着霍仲珍娶的,大家都想看他的笑话,而霍仲珍的表现也果然未令众人失望,曾经再多的感情也被现实浇熄,剩下的只有无尽的嫌恶。
当从前那些讨好凡子的霍家子弟一个个变了模样,想方设法地去欺负这个傻弟妹时,霍仲珍不仅不去维护,反而跟着众人一起教训她。
尤其是有一次,寒冬腊月里,霍家大少夫人非说凡子偷了她的手镯,把她衣服脱得只剩一件,仍未搜出后,罚她跪在门前雪地里,不交出来就不许起身。
霍仲珍赶去时已经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凡子在风中老老实实地跪着,只要稍微动弹一下,身后负责看守的老仆就会抡起手里的烧火棍,狠狠打向她的腿。
衣服下的皮肤已经青一块紫一块,她是被打怕了,毕竟傻子也是知道疼的。
当霍仲珍挤进人群时,凡子的眼眸明显一亮。她已冻得面无人色,伸手去拉他的衣袖,却还记得哆嗦着给他一个笑:“娇娇,冷。”
是的,笑,从前她就最爱笑,即使痴傻了后也还是爱笑,被人欺负了也很少哭,总是一个人在那傻乐。
可这回的笑实在有些勉强,可见真是冷极了。霍仲珍披着厚厚的斗篷,被她拉住衣袖也没什么反应,只是眸色深沉地盯着她,看不出悲喜。
见他没有说话,凡子又摇了摇他的衣袖,语气愈发委屈了:“娇娇,冷,真的……好冷。”
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霍仲珍薄唇紧抿,忽然手一扬,一记耳光狠狠扇去,将凡子掀翻在了雪地里—
“知错了吗?”
一声厉喝响彻长空,这猝不及防的一幕不仅让围观众人惊呆,更是把凡子整个打蒙了,她倒在雪地里久久未动,而霍仲珍还在怒声追问:“为什么要偷大嫂的手镯?”
身子一颤,凡子这才捂住脸回头。她拉住霍仲珍的衣袖,神情有些慌乱:“没有,没有偷。”
再傻的人也知道本能地辩解,而霍仲珍却完全听不进去,抢过老仆手中的烧火棍就往她身上打去,打得她不住躲闪,瞬时红了眼眶:“没偷,没偷手镯……”
凄声回荡在风雪中,打了好一会儿,不知何时,看够了戏的大少夫人才咳嗽两声,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手镯已经找到了,原来是被猫叼了去,弟妹不好意思了……五弟不会介意吧?”
沾了血迹的烧火棍落入雪地里,霍仲珍喘着气,不知过了多久,转过身弯下腰:“大嫂哪里的话,找到就好,找到就好……”
他随手拉起地上伤痕累累的凡子,腰弯得更低了:“既然误会一场,那仲珍先带子回去了,扰了大嫂的清平,实在抱歉。”
冷风呼啸,这一年的冬天当真是极冷,离去时凡子被霍仲珍牵着,歪歪扭扭地跟在他后面,嘴里还翻来覆去念叨着:“没偷,没有偷……”
但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回应她,霍仲珍甚至连斗篷都舍不得脱下来为她挡一挡。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雪地里,很快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只留下身后一路血迹,触目惊心地蜿蜒在白茫茫的一片大地上。
所有人的目光在这时……终于多了一丝怜悯。
霍仲珍是最识时务的,大家都这样说,薄情寡义、趋炎附势,能做到他这个地步的,也是种本事,所以当族长越来越器重他,甚至连夜传见他,似有重要任务交给他时,众人也未感到有多意外。
暖烟缭绕的内室,老族长的声音徐徐传来:“霍大那帮兔崽子都嫌累不愿接担子,还是仲珍你务实,那这次举族南迁的事就由你负责了……”
霍家近年生意重心南移,整个家族也要迁宅了,这门没什么油水的苦差事推来推去,推到了霍仲珍头上,他倒也欣然应下。
只是老族长接下来的话叫他一愣:“迁宅是大事,找风水师算了,偏不巧仲珍你媳妇与新址相冲,你看这……”
老族长叹息着,似有为难。霍仲珍跪着久久未动,夜风一下又一下地拍打着窗棂,他眨了眨眼,终是将头埋了下去,无悲无喜:“子她就……留在老宅吧。”
动身那天,凡子跌跌撞撞地追了出来,手里还抓着幼时初见霍仲珍送的那只兔子木雕。
她在马车后面追着,一边招手,一边喊着:“娇娇,娇娇你忘了我,还有我呢……”
身上是霍仲珍给她置办的新衣裳,头上是霍仲珍给她买的新发簪,她这段时间特别开心,因为娇娇对她特别好。只是她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出去玩,娇娇会忘了带上她?
浩浩荡荡的车队绝尘而去,有人掀开车帘探出头,正是最后望了凡子一眼的霍仲珍,只这一眼,便如福至心灵,叫凡子整个人都慌了起来:“娇娇,娇娇你们去哪里?”
她追得更急了,连留下来看管她的老嬷嬷都拉不住,裙角翻飞间,她不防摔倒在地,扬起一地尘埃—
“娇娇!”
凄厉的一声呼唤,她浑身剧颤,仿佛明白了什么,握住兔子木雕的那只手抖得不成样子。
直到马车彻底消失在眼前,被死死按在地上的凡子终于崩溃,满脸尘土的她“哇”的一声,号啕大哭,哭声响亮,连前方马车里的霍仲珍都能隐约听到。
这是他第一次听她哭得这么凄厉,她那样爱笑的一个人,无论怎样受欺负都能自得其乐,原来哭起来也会这样撕心裂肺,撕心裂肺到让他不敢回头……
承平十四年将她遗弃,承平十九年回来寻她,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霍仲珍终于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以霍家新任族长的身份。
老宅门口,依旧是那辆马车,但这回,凡子却怎么也不肯上去。
她抓着兔子木雕,脸上明明笑嘻嘻的,眼里却透着惊恐,霍仲珍知道,她是有阴影了。
所以他眼眶酸涩,一个打横将她抱了上去:“子,别怕,不会再有人把你扔下了。”他贴在她耳边,字字温柔。
风掠长空,凡子勾住霍仲珍的脖子,眨了眨眼:“那影子君呢?”
霍仲珍一愣,凡子又问:“娇娇,我能把影子君也带回去吗?”
大眼瞪小眼了半晌,霍仲珍哑然失笑,心口却酸酸的。他重重点头:“能,以后子想要什么都行。”
说这话时他并没有看见,凡子对着他身后做了个鬼脸,而空中也似有清风拂动,抖落一树笑声。
马车上,霍仲珍情不自禁摸向凡子耳后的一处伤口,那是当年他在雪地里掌掴她留下的旧疤,如今指尖一寸寸摩挲着,仿佛闪过往昔的一幅幅画面。
凡子有些痒,乐呵呵地想要躲开,却忽然被霍仲珍一把扯入了怀中,脑袋直接撞上他胸口。
车马颠簸,那一瞬,她听见了他强有力的心跳。怆然落下的泪珠,滑入脖颈中,温热一片。
凡子一定不会知道,这五年,霍仲珍经历了些什么。那些血腥与肮脏,他也永远不会让她知道,她只需知道,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够欺辱她了。
从前他不争不夺不斗,只因他没什么想要的,但从凡子衿死牢里出来的那一刻,他想要的就太明确了。
世人欺他辱他,无谓;世人欺她辱她,妄想!
为此他选了一条极其艰难的路,或许懵懂如她,永不会懂他的隐忍蛰伏,但没关系,那些都过去了,他的好姑娘从来不记仇,他还有余生大把的时间去好好爱她——
就像凡子衿曾说过的那样,他去为她厮杀一片天,而此后漫漫余生,她只要做他的小白兔,永远那样笑着就行。
马车里,风吹帘幔,虚空中似有幻影浮动,俯视着这一切,发出了不知何意的轻叹。
将凡子以盛大的仪式迎回霍家后,霍仲珍很长一段时间觉得此生再无所求,但渐渐的,他觉得有些不对劲了,有件事不得不引起他的注意了,那便是凡子成天挂在嘴边的“影子君”—
花园里,他问她为什么总是一个人玩,她头一歪,笑得天真烂漫:“有影子君陪我玩呢。”
戏台前,她对着他精心准备的惊喜呵欠连连,溜走后被他逮住,还无比委屈:“影子君说不好听,还没他唱的曲子好听呢,我也这样觉得。”
最过分的是,夜间就寝时,他情不自禁吻上她的唇,这都不可以,原因是“影子君说了,这里不能随便给人碰,玩游戏也不行”。
他终于对这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影子君”来火了,质问凡子:“可我是你夫君也不可以吗?”
怀里的姑娘像小白兔一样,委屈地摇了摇头。于是他只好按捺住怒火,试探问道:“那谁可以?”
哪晓得她竟想也不想,脱口而出:“影子君可以。”
那一瞬,月光洒入屋内,映着凡子笑靥如花的一张脸。霍仲珍几乎咬碎银牙,他有理由怀疑自己曾经的一些理解出错了,那么他想知道—
这“影子君”究竟是何方神圣?
如果说之前的种种迹象还只是怀疑,那么当在凉亭里,见到凡子绘出的那张画后,霍仲珍才是真正震惊了。
他们不过在亭中赏花,他忽然兴起,要她为他作幅画。她丹青一向是极好的,即使摔坏了脑袋,从前的功底也还在。
只是霍仲珍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他在花间站得腿都酸了,终于接过画时,却见到那样一幅场景—
画中人云衫飘飘,嘴角噙笑,一手提着酒壶,一手枕着脑袋,醉卧花间,端得芝兰玉树,潇洒不羁,竟是个从未见过的陌生男子!
瞳孔骤缩,霍仲珍赫然转头,却见笔墨未干的石桌前,凡子撑着下巴,冲虚空笑得眉眼弯弯,和曾经无数次自言自语时一样。
他呼吸一窒,有什么在电光石火间终于明白过来,手指剧烈颤抖着,他抓紧那幅丹青,脚步踉跄地奔出凉亭,是从未有过的激动:“谁?谁在那儿?”
他像发了疯般,在所有奴仆惊诧的目光中,拂袖乱挥,踏断一丛丛花枝,几乎血红了双眼:“你就是那个‘影子君’吗?你是何方山野精怪,我不怕你,你出来啊,不要再缠着我娘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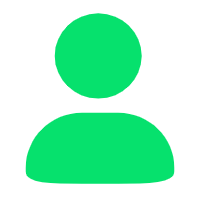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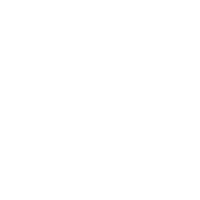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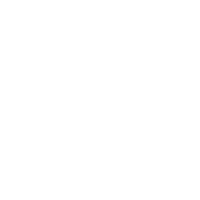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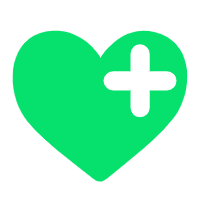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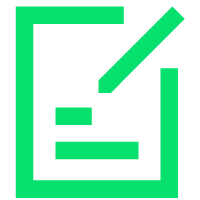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哦,快来首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