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女千语
说完一拂袖,踏风而去,站在原地的顾思桐捂住嘴,整个人都傻掉了。
遇见纪元甫是在十三岁,在那之前,宋凉宛还没有成为宋家的一朵奇葩。
她从小虽是舞刀弄枪,大祸小祸不断,但大抵还算个“正常人”。
这是宋锦夜对妹妹的评价。宋凉宛当然不认同,在她看来,就是遇上纪元甫后,她才“重获新生”—
百种口技,百样人生,百变新生。
纪元甫是淮都衙门的师爷,生来腿有残疾,被遗弃在府衙门口,叫当时打光棍的纪捕头捡了回去,认作干儿子。
纪捕头粗人一个,养大的纪元甫却是清俊文秀。一袭青衫,坐在轮椅上翻书的身影像幅画卷,同院中漫天飘洒的梨花,一并入了来寻他的宋凉宛眼中。
那年宋凉宛才十三岁,在淮都知府的寿宴上遇见纪元甫,从此一见倾心,念念不忘。
对于纪元甫,宋凉宛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淮都知府大寿,邀请一众达官贵族赴宴,其中一个节目叫作《百鬼夜行》。
灯烛尽灭,月光洒入屋内,一道屏风隔开众人,屏风后开始发出第一声幽叹。
如一个信号般,紧接着是风掠竹林之声、花精、雀妖、女子媚笑、书生哭泣、老者赶路……各种声音,各种画面,层层叠叠,惟妙惟肖,仿佛这屋子里真的藏了一座百鬼林。
所有人都听得入迷了,尤其是宋凉宛,她不过半大的孩子,正是好奇的年纪,又是第一次接触到所谓的“口技”,整颗心简直都被吊起来了。
当百鬼放歌,唱完最后一个音节时,灯烛骤亮,满屋人如梦初醒,不知谁带头鼓起了掌:“奇哉,奇哉,当真闻所未闻!”
而宋凉宛更是站起,不顾父亲的阻拦,径直朝屏风后走去:“我不信,这么多种声音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发出来的,后面一定藏着什么!”
她一步并作几步地掠到了屏风后,才一站定,整个人就愣住了——
一双眼,一双清冽入骨的眼。少年面目俊秀,孑然一人,坐在轮椅上的身影就似一幅画。
四目相对,宋凉宛久久未动,像一刹那被击中,周遭喧嚣迅速退去,倏忽置身于山野天地间,头顶月,耳边风,眼里心里只能望见他。
后来她才知道,有个词叫作——平生一顾,至此终年。
而彼时直到少年一声咳嗽,向她点头致意:“见过宋三小姐。”她才怔怔回过神来,少年却已转过轮椅,默默入了后堂,消失在了她的视线中。
那一夜,宋凉宛明明滴酒未沾,却像醉了一样,走路都是飘的。她回去后在屋顶上闹了半宿,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疯魔了般。
宋锦夜跑出来大喊:“凉宛你闹够了没?快给我滚下来!”
她却笑得更欢了,提着裙子转圈,双手拢在嘴边,仿佛向全世界宣告:“纪元甫,他叫纪元甫!”
笑声飘在风中,她一双眼睛亮晶晶的,对着宋锦夜大声道:“二哥,我要拜他为师,我要跟他学口技,你说好不好?”
说完一拂袖,踏风而去,站在原地的顾思桐捂住嘴,整个人都傻掉了。
遇见纪元甫是在十三岁,在那之前,宋凉宛还没有成为宋家的一朵奇葩。
她从小虽是舞刀弄枪,大祸小祸不断,但大抵还算个“正常人”。
这是宋锦夜对妹妹的评价。宋凉宛当然不认同,在她看来,就是遇上纪元甫后,她才“重获新生”—
百种口技,百样人生,百变新生。
纪元甫是淮都衙门的师爷,生来腿有残疾,被遗弃在府衙门口,叫当时打光棍的纪捕头捡了回去,认作干儿子。
纪捕头粗人一个,养大的纪元甫却是清俊文秀。一袭青衫,坐在轮椅上翻书的身影像幅画卷,同院中漫天飘洒的梨花,一并入了来寻他的宋凉宛眼中。
那年宋凉宛才十三岁,在淮都知府的寿宴上遇见纪元甫,从此一见倾心,念念不忘。
对于纪元甫,宋凉宛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淮都知府大寿,邀请一众达官贵族赴宴,其中一个节目叫作《百鬼夜行》。
灯烛尽灭,月光洒入屋内,一道屏风隔开众人,屏风后开始发出第一声幽叹。
如一个信号般,紧接着是风掠竹林之声、花精、雀妖、女子媚笑、书生哭泣、老者赶路……各种声音,各种画面,层层叠叠,惟妙惟肖,仿佛这屋子里真的藏了一座百鬼林。
所有人都听得入迷了,尤其是宋凉宛,她不过半大的孩子,正是好奇的年纪,又是第一次接触到所谓的“口技”,整颗心简直都被吊起来了。
当百鬼放歌,唱完最后一个音节时,灯烛骤亮,满屋人如梦初醒,不知谁带头鼓起了掌:“奇哉,奇哉,当真闻所未闻!”
而宋凉宛更是站起,不顾父亲的阻拦,径直朝屏风后走去:“我不信,这么多种声音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发出来的,后面一定藏着什么!”
她一步并作几步地掠到了屏风后,才一站定,整个人就愣住了——
一双眼,一双清冽入骨的眼。少年面目俊秀,孑然一人,坐在轮椅上的身影就似一幅画。
四目相对,宋凉宛久久未动,像一刹那被击中,周遭喧嚣迅速退去,倏忽置身于山野天地间,头顶月,耳边风,眼里心里只能望见他。
后来她才知道,有个词叫作——平生一顾,至此终年。
而彼时直到少年一声咳嗽,向她点头致意:“见过宋三小姐。”她才怔怔回过神来,少年却已转过轮椅,默默入了后堂,消失在了她的视线中。
那一夜,宋凉宛明明滴酒未沾,却像醉了一样,走路都是飘的。她回去后在屋顶上闹了半宿,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疯魔了般。
宋锦夜跑出来大喊:“凉宛你闹够了没?快给我滚下来!”
她却笑得更欢了,提着裙子转圈,双手拢在嘴边,仿佛向全世界宣告:“纪元甫,他叫纪元甫!”
笑声飘在风中,她一双眼睛亮晶晶的,对着宋锦夜大声道:“二哥,我要拜他为师,我要跟他学口技,你说好不好?”
宋锦夜气疯了:“好好好,好你个大头鬼!”
便是从这天起,宋锦夜觉得,他家小妹彻底放弃正常人的身份,从此走上了一条奇葩的不归路。
起初纪元甫不愿收宋凉宛为徒。
她找到他时,他正在梨树下看书,闻言转了轮椅,淡淡婉拒:“供人赏乐的小玩意罢了,宋三小姐学来做什么?”
宋凉宛不好意思说出那句“因为你”,便掸掸袖子,装出一副正义凛然状:“为了给世人带去更多乐趣,让苍生少受一些痛苦。”
纪元甫瞥了她一眼,以看失心疯的目光,没有说话,只是转过轮椅,不再理会她。
此后一个不肯,一个偏要,反正宋凉宛脸皮厚,便跑过来天天相缠,还自发自觉地叫起了“师父”。
终是有一天,纪元甫忍无可忍,在树下对宋凉宛道:“若要学百种口技,需先体会百样人生,你若真有那个毅力,再来找我吧。”
他的意思很简单,想模仿什么口技就先过什么生活,模仿摊贩就自己去摆摊,模仿舞姬就自己去跳舞,百样人生才能换来百种口技。
其实这种说辞不过是蒙宋凉宛呢,想让她知难而退,哪晓得宋凉宛一根筋,竟像得到宝典秘诀般,拱拱手,欢天喜地地去了。
这一去,就是一个月。
宋家都快急疯了,翻遍整个淮都也没能找到失踪的宋凉宛。满城风雨中,唯有纪元甫知晓内情,但他也不清楚宋凉宛去哪了,他极其不安起来,夜夜难眠,从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
就在所有人都揪着一颗心的一个寻常黄昏,宋凉宛回来了。
起初纪元甫没认出她,他只是随手给经过他家门前的小乞儿端了碗水,那乞儿蓬头垢面,看不清模样,声音倒是很秀气,还带丝怯意。
“谢谢大哥哥。”
他点点头,依旧愁眉不展,那乞儿同他说了好些话他也没听进去,最后耳边忽然响起一声尖叫,一个熟悉的声音欢呼起来:“我成功了,师父你都没认出来,我成功了!”
他身子一颤,那小乞儿将脸上黑炭三五下抹去,露出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望着他眉开眼笑。
“你……”巨大的冲击让纪元甫一时说不出话来,好半天,他才转过了轮椅,肩头微微抖动起来。
宋凉宛奇怪地凑上前,才蹲下身,就发出了一声惊呼:“呀,师父,你怎么哭了?”
风掠长空,衣袂翻飞,纪元甫忽然伸手,将宋凉宛一把拉入了怀中。
宋凉宛猝不及防,脑袋直接撞到了纪元甫的胸口,那一刻,天地间仿佛都静了下来。
心跳挨着心跳,气息萦绕,有热泪流入脖颈,宋凉宛颤了颤,却一动也不敢动。
夕阳笼罩着他们,将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有梨花悠悠落下,同他们一并入了画。
一场鸡飞狗跳的风波就此收场,事后宋凉宛坐在树下,对着纪元甫喋喋不休:“师父,我在乞丐堆里混了一个月,每天往城门口那儿蹲着,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学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对了,我还结识了一帮好兄弟呢,大家住在一个破庙里,我跟他们说我叫芋头,他们都可喜欢我了,说我机灵,有什么好吃的都先想着我,倒是没受多大苦……”
纪元甫忽然打断:“为什么叫芋头?”
宋凉宛一愣,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师父……是圆子啊。”
她眨着眼,脸上染了红晕,却还是定定地望着纪元甫:“你是圆子,我是芋头,多般配。”
熟识后她从不掩饰对他的喜欢,没羞没臊的话飘入风中,纪元甫咳嗽一声,转过轮椅,长睫微颤。
“谁允许你给我起这么奇怪的绰号了?”
风过长空,梨花悠然,宋凉宛忍俊不禁,笑声如银铃般,在整个小院久久回荡着。
“你要走?”
溜进衙门后堂的宋凉宛,依旧一副军师装扮,蹲在纪元甫的轮椅前,瞪圆了眼。
纪元甫点点头:“对,去丰城执行公务,那里正闹瘟疫,我要代表淮都府衙前去赈灾派粮。”
“那……要去多久?”宋凉宛可怜兮兮地问。
“还不清楚。”纪元甫伸出手,将宋凉宛唇边粘的胡子撕下,微皱眉头,“听说你又惹祸了?把你二哥的新娘都吓住了?”
宋凉宛嘿嘿一笑,有些不好意思,但紧接着又换上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我要跟你一起去。”
“不准。”纪元甫果断拒绝,眸光深深,“你这些年也玩够了,我已没什么可教的了,你二哥都娶亲了,你也该收心了,日后……还是少来这里吧。”
说完,他竟下了逐客令,转着轮椅就把宋凉宛往屋外赶。宋凉宛被推搡得跌跌撞撞,两只手抠着门框不肯走。
“师父,师父你又要赶我走,别啊,我才来呢,师父……圆子!”
一声大喝,一个低头,一个仰头,四目相对中,空气都瞬间凝固了。
许久,纪元甫嘶哑开口:“这么多年了,何苦呢?”
头一年,她认他为师,他不好食言,开始随便教她些口技,以为她很快就会厌倦,将兴趣转向别的新鲜事物,但她没有。
第二年,她缠他缠得更厉害了,除了学口技外,还天天跑来给他打扫屋子,为他请大夫看腿疾,忙前忙后地给他抓药。街坊四邻不清楚的,还以为纪捕头给他找了个童养媳。
等到第三年,她及笄了,有人上宋家提亲,她装神弄鬼把媒婆吓走,还去学给他听,笑得前仰后合。他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是坐在轮椅上喃喃:“你这样胡闹会嫁不出去的。”
她坐在树下喝酸梅汤,抹了把嘴,抬首一本正经:“可我是芋头啊,我喜欢的是圆子,我不想嫁给别人。”
…………
这么多年了,她对他的喜欢从不避讳,永远没羞没臊、掷地有声,但却是一个往上凑,一个往外推—
只因没有人比他更清醒。
“别再谈喜欢了,一个是淮都宋家的三小姐,一个是身患腿疾的穷酸师爷,这份喜欢,你以为能有多少圆满的可能?”
硬生生地掰开宋凉宛的手,纪元甫直接关门送客,他坐在轮椅上,后背抵着门,任宋凉宛在外头大呼小叫地拍门。
他久久未动,只是苍白着脸,失神地望向虚空,眼眸蒙了层雾般,深不见底。
这年盛夏,纪元甫领队出发,押着赈灾粮,向丰城浩荡而去。
出发没多久,某天原地休息时,有侍卫上马车端水给他喝,他喝到一半,忽然一把扣住那人的手腕,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宋凉宛,你有意思吗?”
那小侍卫受到了惊吓,哆嗦着抬头,是张完全陌生的脸:“小的……小的是新来的,不知道师爷在说些什么……”
纪元甫深吸口气,手下用力,刚想开口,马车却猛地一颠,生生刹住,外头一阵兵荒马乱,传来遥遥一声—
“停车停车,打……打劫!”
尘烟滚滚,旗帜飞扬,山道上忽然冲出一帮劫匪,将运粮队团团围住,来势汹汹。
一片混乱中,那小侍卫挣脱纪元甫,反手一把背起他,掀了车帘就往外冲:“快,师爷,我保护你逃走!”
外头刀光剑影,一片打杀,他背着纪元甫横冲直撞,不要命地突出重围。纪元甫在他背上不住挣扎着:“凉宛,凉宛你这个时候还装什么,别管我了,自己快逃!”
就在局面混乱不堪时,几匹高头大马忽然停在了小侍卫身前,将他连同纪元甫三面围住。
“想逃?”为首的匪头红袍烈烈,居高临下地打量着他们,嗤之以鼻,“官家的师爷就这般没种吗?”
他语调熟悉,听得小侍卫一个激灵,猛地抬起头,果然对上了那几张记忆中的脸。
“大钱、小结巴、龙烈!”
脱口而出间,他激动不已,又难以置信:“我天,你们怎么做土匪了?!”
马上的几个人明显一愣,面面相觑,正摸不着头脑时,那小侍卫将背上的纪元甫一把放下,伸手就往脸上摸,发丝飞扬,瞬间露出本来面目:“我,我是芋头啊!”
人生四大喜,其中一条是“他乡遇故知”。
时过境迁,当年破庙的一群小乞儿四分五散,从没想过会在这种情况下遇上。
匪头龙烈一甩红袍,下马便将宋凉宛抱起,狂喜地转起了圈。
一场官匪大战意外而止,龙烈没转几圈却忽然停住,在风中望向宋凉宛,神情有些古怪:“芋头,先不说你怎么入了官家,你那胸口……莫不是垫了馒头?”
话落音,地上的纪元甫脸色都变了。
把宋凉宛和纪元甫送出龙头寨,龙烈颇有感慨,小弟成了小妹,乞儿成了山匪,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世间事当真太过奇妙。
山下运粮的队伍整装待发,宋凉宛推着纪元甫的轮椅,临行前,看着龙烈欲言又止:“阿烈,你身手好,人又聪明,实在没必要带着兄弟们干这个……”
龙烈红袍一扬,剑眉星目,在阳光下笑得无奈又洒脱:“世道艰难,官逼民反,活不下去了只好上山为匪,占地为王,做点劫富济贫的事。”
“放心,你阿烈哥走的路虽不是什么正途,但也坏不到哪儿去,我自有分寸。”
未了,他反将宋凉宛拉到一边,语带不忿:“倒是你,难道真看上那个瘸子师爷了?”
宋凉宛皱眉,压低声音:“什么瘸子师爷,不过是生下来就带的腿疾,又不是他的错,阿烈你别这样说他,我不高兴。”
“好好好。”龙烈举手认输,满眼无奈,“我只是担心你,现在丰城闹瘟疫,遍地死尸,你自己要多加小心,收好我给你的信号弹,一有不对就通知我们,反正丰城离龙头山也不远,我们看到信号就会赶去,听清楚了吗?”
宋凉宛感动万分,在飒飒风声中,抱了抱龙烈,又一拳捶在他胸口,吸吸鼻子:“好兄弟,够意思!”
直到宋凉宛与运粮队离开很远后,龙烈仍站在山头眺望,他伸出手揉了揉被宋凉宛捶过的胸口,不知怎么,竟升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
少刮点风吧队伍重新上路,马车里纪元甫问起方才说了些什么时,宋凉宛笑笑,撑着下巴望着他。
“阿烈呀,他说你长得可好看了,丰神俊秀的,一看就是饱读诗书,人中龙凤的那种,怕我大大咧咧、毛手毛脚的,配不上你呢!”
纪元甫没好气地一弹她额头:“你还真当我是三岁小儿呢。”他摇摇头,望向窗外,“罢了罢了。”
车里帘幔飞扬,无端端地就弥漫起一股心照不宣的哀伤,不知过了多久,宋凉宛忽然上前,从身后环住了纪元甫的腰。纪元甫一颤,她却将脑袋靠在了他肩头。
窗外的风迎面吹来,两个人都没有动弹,纪元甫只感觉到背上温湿一片,许久,宋凉宛才闷闷开口:“圆子,不管别人说什么,你都是我的圆子,所以……请你不要再把我推开了,好不好?”
即便做了心理准备,但丰城的惨状还是超出了宋凉宛的想象。
纪元甫不准她出去,自己却天天在外面派粮,每每深夜才回。
他一回来,宋凉宛就扑上去扒他衣裳,将他连人带衣都泡到艾叶水里,泡个彻彻底底。
纪元甫争不过,又疲乏不已,一来二去,便也随着宋凉宛了。
她给他擦身、熏香、涂药……总之从里到外都武装起来,生怕被那无孔不入的瘟疫入侵。
纪元甫从没想过,宋凉宛也有这样细心的一面,他说起时,她倒毫不谦虚,得意扬扬:“那当然,我是谁!”
“你说,要是我没跟来,你身边没个人服侍,多不方便?”
夜色迷蒙,风拍窗棂,纪元甫泡在浴桶里,水雾氤氲间,看不清他脸上的神情。
“这些事我自己也可以做。”
宋凉宛站在他背后,一边给他涂药水,一边扬眉:“那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过了许久,纪元甫都没听到回答,正要扭头看时,宋凉宛已不知何时绕到他身前,飞快地在他唇上轻啄了一下,笑得狡黠而又霸气:“就是这个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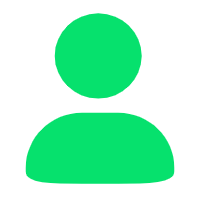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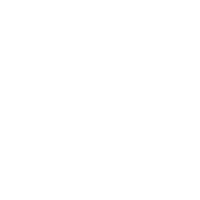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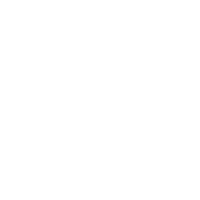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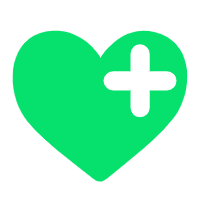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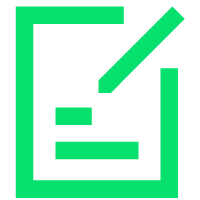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哦,快来首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