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
是抱在怀中,该是多么可人的模样。
“啪”,她把笔拍在笔山上,将脸埋进了双掌间。
孟晴,你真是有毛病……她骂道。
“嘶……”
“疼吗?你这淤青还带着撕裂伤,这药涂上去肯定会疼。”
寝室内隐约传来二人对话的声响,孟旷的魂立刻全都被牵了过去。她不自觉地站起身来,缓缓踱步到内门边,透过琉璃隔扇观望着室内的景象。但是入眼却是一片模糊,只能瞧见影影绰绰的人影在室内几盏灯火的照耀下摇曳生姿。
孟旷后悔了,她方才为什么要说自己忙?她真的很想看看穗儿的伤,这些年的遭遇给她留下的惨痛伤痕,孟旷希望自己都能看在眼里。那些新添的淤伤,又是怎么来的?她也想问清楚。
“你真的不愿说是谁打的你吗?”孟暧低声的询问响起,她一边为穗儿上药,一边又试探了起来。
“其实,这伤是我自己弄的,和别人无关。”穗儿居然答话了。
“胡说,你自己怎么能打到自己的后背,这分明是有人用棍棒之类的东西打的,这伤可骗不过我的眼睛。”孟暧道。
穗儿淡淡回答道:“宫中有一种刑罚用的工具,叫做自纠棍。那是竹制的,很长,向上甩到头顶,棍头的竹片不曾绑紧,韧性很强,恰好可以甩过来打到后背上。犯了错的宫人,若是主子怜悯,让他领自纠棍,便是自己打自己,一左一右算是一下。我犯了错,领到的刑罚是打自纠棍,打出血为止。”
孟暧涂药的指尖缓缓颤唞起来,孟旷伏在背后的双手渐渐握成拳。
孟暧问:“你犯了甚么错?”
“我没有犯错,只是别人犯了错。”穗儿笑了,“我替她顶了。”
“你可真傻。”
“我若不替她顶了,她定比我现在还要难过。反正……我不久后也要离宫了,在我离开前,若是能帮一帮别人,也算是积了功德。”
“是哪位主子罚得你?”
“贵妃娘娘。”
“贵妃……就是那位郑贵妃吗?”孟暧问道,她对宫中有哪些主子不是非常清楚。
“嗯。”
孟旷眸光浮动,莫非她口中所谓落了裁缝包在郑贵妃那里是真事儿?只是她并非当真撞破了郑贵妃的秘密,或许裁缝包也不是她落下的,但应当确实是她回去取的,然后可能中间又出了什么事,让她领了罚。
眼下宫中有传言,郑贵妃情绪不稳定。因着她眼下已有九个多月的身孕,正是临盆在即。她所在的承乾宫上下都很紧张,宫人经常会因为很小的事而被罚。
孟暧没有再细问,转了话题道:
“刚刚为啥不让我姐来帮忙?”
“……我不大想让她看到我的身子。”穗儿踌躇着慢慢说道。
“呵呵,我姐虽然女扮男装好些年,但她还是女人呀,这有什么好害羞的。而且九年前,你刚来我们家那天晚上,就被她看光了呀,她可是替你洗过身子的人。”孟暧觉得好笑。
站在隔扇后的孟旷也缓缓弯起唇角。
“也不是……害羞……”穗儿这话说得没甚说服力,面庞绯红的,“我现在的身子,比那时丑多了。”
这话说得孟暧和孟旷心中猛地一酸。
“丑甚么,还能嫌弃你咋的?”半晌,孟暧似是有些气呼呼地说道。
这话倒是引得穗儿笑了。
“好了,药上好了,我给你简单裹了一层纱布,你夜里睡觉尽量侧着身子睡,压着伤口不大好。”孟暧上完药,一边收拾药瓶,一边叮嘱道。
穗儿一面点头,一面拉起衣服穿好。眼瞅着孟暧就要过来了,孟旷忙三步并作两步地回到了书案后坐下,拿起笔来,装作冥思苦想的模样。
不一会儿孟暧开了内门进了书房,一眼瞧见孟旷坐在那儿,桌面上那张纸方才是多少字现在还是多少字。她不禁暗暗笑了,心道阿姐方才估计根本就是在偷听罢。
“姐,你的毯子,我给你放床上了。”
“哦。”孟旷抬头应了一声。
她瞧孟旷半湿半干的长发简单束在脑后,身上衣衫也很单薄。想起自己还披着姐姐的衣服呢,于是脱下袄袍,走过来披在姐姐身上,道:
“你别仗着自己身体好就逞能,当心着凉。”
“嗯,我省得。”袄衫还带着孟暧身上的温度,暖暖的熨贴着孟旷的心。
“别累着自己了,早点睡,我也去歇了。”
“好。”
“晚安,姐姐。”
“晚安。”
孟暧带了书房的门出去了,孟旷的视线则落在了那放在罗汉床上的毯子上。她不自觉地起身,走到罗汉床边拿起了那条毯子,触手间还有些温湿。隐隐约约鼻端传来一阵清香,她缓缓将那盖毯凑近鼻端轻嗅,那似是兰花的香气。这是她身上的香味吗?怎不知她还有体香,莫不是这些年在宫中熏香带出来的。可前几日也没闻到呀,沐浴才会有吗?
冷不丁内门出传来了穗儿的声音:
“旷哥哥……我能进来吗?”
孟旷吓得浑身一颤,忙把那盖毯胡乱一团,塞到了罗汉床的一角。自负了双手,立在一旁装若无其事。
“你要作甚?”她生硬地回道。
“我想……借本书瞧瞧,可以吗?”
“你要看甚么书,我给你拿。”她道。
“我……我也不知道……”穗儿无奈道,她只是想借本书打发时间,一时间也不知道自己想看什么书。
书房内半晌没有反应,穗儿本以为孟旷不理她了,轻叹一声。刚准备返身回床榻休息,内门就开了,孟旷手中持着几本书出现在门口。
穗儿盯着她愣怔起来,总觉得她这气鼓鼓的模样,不像是来借书的,倒像是来讨债的。这人似乎总是在生气,生各种各样的气,或森冷,或肃杀,或爆裂,或悲怆,如今却又是另外一种气,是什么呢?她搜肠刮肚思索着辞儿想要去描述,却一时不知该用什么辞了。
孟旷走了两步,来到穗儿近前,把那几本书塞进她手里。随即突然说道:
“你莫喊我旷哥哥。”
“嗯?”穗儿不解。
“总之就别喊。”
“那我……该如何……”
“随意!”她粗鲁地打断穗儿的询问,转身回了书房,内门又一次关上了。
穗儿无言地在原地愣了一会儿,随即将注意力转到了手中的书上,第一本是《汉乐府诗集》,第二本是《吕氏春秋》,还有一本《近思录》。她随手翻开了乐府诗集,不曾想直接就翻到了《有所思》,因着孟旷在这一页上折了角。她默默读着这首乐府诗,心下倏然升起一股不可明说的喜悦,这喜悦真是没来由,让她全然不理解。但她心下忽的就欢然起来,方才孟旷那气鼓鼓教她莫要唤她“旷哥哥”的模样,在脑海中也显得可爱起来。≡本≡作≡品≡由≡思≡兔≡網≡提≡供≡線≡上≡閱≡讀≡
她笑意盈盈地走回到桌畔,为油灯罩了罩子,打算今夜长读解闷。却不曾想,身子刚撑到桌边,“咔嚓”一声,这可怜的桌子终于断了腿,倾覆翻倒过去,油灯也打破在地。
“怎么了?”孟旷听到动静迅速开了门进来,一眼就瞧见穗儿狼狈又无奈地坐在翻倒的桌子边。
孟旷瞧着那断了腿的桌子,登时尴尬起来。油灯也打翻了,屋内一片黑暗。默了半晌,她闷闷道:
“我明儿来修,给你换一张桌儿。”
“嗯。”穗儿半含着笑意应道。
“你……今夜还读书吗?”
“想读。”
“那……你且来书房罢。”孟旷踯躅着说道。
穗儿在黑暗中展露出了欣然的笑容。
第22章
穗儿收拾了散落在地的书本,缓缓步入书房时,孟旷正收拾了书案上东西,似是将一张纸悄然塞进了袖筒。
她扭身,见穗儿站在身后,便指了指书案后的圈椅,道:
“你坐这儿看罢,我困了,先睡了。”
说罢便坐到罗汉床边,展开被毯钻入其中,面朝里侧,默默睡去,不再理会穗儿。穗儿抿了抿唇,依着她的话儿坐在了书案后,将油灯罩子调整了一下,遮住往她那里照去的光,将光芒聚拢在自己身前。
她禁不住抬眼望她,见她卧在罗汉床上一动不动的模样,心里丝丝缕缕的,牵起了道道思绪。再翻开《汉乐府诗集》,那首《有所思》,当真是让她读入了迷。想起自己重回孟家的第一个夜里,或许她也如现在的自己这般,坐在这书案后等着天明。天微微亮时,便再也熬不住出了屋,挥舞起螣刀,宣泄繁杂的思绪。
是这样的吧,穗儿私心里真希望孟旷确如她所猜想得那般,希望自己不是自作多情。
“你莫唤我旷哥哥。”冷不丁她方才的话语又在耳畔回响,穗儿凝着眸子思索。为何不愿自己唤她“旷哥哥”,也许此情杂然难为外人道。但穗儿却能体会一二,莫不过是气闷与伤感。她到底还是个女子,总听人唤她“哥哥”,便总不住地被提醒她其实是女扮男装身不由己,心里有气也是必然。真正的旷哥哥眼下有家回不得,流浪外地不知何时归,她其实也对哥哥有着万分的思念,总听人念叨她“旷哥哥”,亦难免勾起伤怀之情。
再者乎,他人这般唤她也无妨了,但偏偏唤她的人是自己,心中就又添了一分堵。如若不是自己,也不会害得她二哥离家,她又女扮男装难以回归寻常的生活。自己确实是有些不知廉耻,不懂体恤,太过唐突了。
想到此处,不禁有些懊恼。之前只是出于简单的“晴姐姐”与“旷哥哥”的对应,她才这般喊的。可,自己却又到底该如何唤她呢?小小的称呼问题,竟成了她眼下最大的烦恼。她多么想能和她说上两句话,总这般僵着可如何是好?若是不能有个讨她欢心的称谓,那真是千言万语都无从说起了。
她撑着下颌,凝望着昏暗中侧卧在罗汉床上的那人,心底不由升起一股怨怼。这人脾气真是坏透了,凶巴巴的,当年那般温柔体贴的晴姐姐,真是一点也不见踪影了。许是这些年在军中受尽磨难才会这般罢,若是脾气太好,可不得受人欺负?何况她还得掩饰身份,自然要凶一点才能与他人拉开距离。长久以来心里都闷着一股气,难免会如现在这般了。
说起来……她扮作男子时可真是没什么破绽,若是不露头脸,真叫人无法想到她竟是个女子。想到此处,脑海中不由浮现出那雪夜寒庙中,她第一次对自己摘下面具时的情景,那张昔年秀美的女子容颜,如今却多了三分的英气,七分的俊俏,真是好看。若是不去想她是个女子,合该是个绝世的美男子。
她那体格,女子中真是少见。比自己高出大半头去,一展臂就把自己整个裹进了怀里。身上的力道也大,掐她、拽她、抱她,真是半点反抗也不得。但却又不似男子那般一身的浑浊气惹人厌恶,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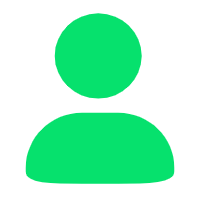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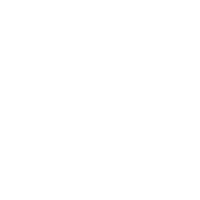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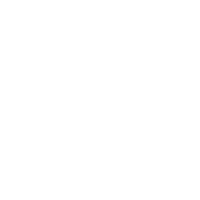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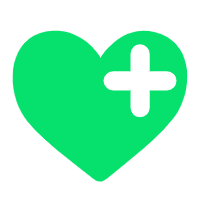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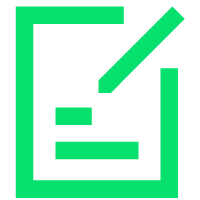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哦,快来首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