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天干物燥,拿头去喝茶
“第四队,21,成皜,收到——求救。”
咬着止血的绷带松了松,成皜用肘部抵住了无线电讯的传音键,费力的回答道。
在被“现象级”䁛驻留的城市发声回复是不明智的选择,但断裂的双手已经无法编译回讯密文了。他大抵是要死了,即便按照作战要求发出求救,但他并不希望有战友前来救援。
一个废人,会拖累队伍的。成皜观察着周围的状况,默默的想道。
他所处位置是一栋建筑的天台,这个尚且安全的位置拥有较好的视野。他的双腿虽然受伤,但还能够行走,只是失去了抓握武器的双手,他注定活不久了。
“21,成皜,是否有行动能力?”头盔内的耳机传来机械音。
“失去双手,仍有行动能力。”
“躲藏,等待救援。”
没有语调的合成音却带着生存的希望飘入成皜的耳蜗,这或许是今天最好的消息。
成皜清楚,他们的人已经不多了。第四队进入灾难区时有一百五十人,进入这里,大家都写好了遗书,只进不出的前三个小队已经为他们的这次行动敲响了丧钟。
但总要有人去的——囊括三个大型城市的灾难,五千万人——灾区的人们需要秩序与希望,他们需要团结活着的人民,等待破局之法。
现在,第四小队只剩五十多人了,在寻找当地治安力量和搜救幸存群众的工作上,有太多人牺牲了。好在,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避难区。小小的避难区奇迹般的扛过了白色枝条的探寻、世界翻转的恐慌,还有黑暗中癔症的癫狂。灾难中求生的人们真是难以想象的坚强。
一撮绿色的野草突兀的出现在天台的阳光房内,之后一团大草跳出了玻璃拼接的围栏,迅速的向成皜蹦跳过来。
这是副队长的伪装诅咒,成皜确信,“区域性”诡一般只会袭击它们认知中的外来者,但却少有诡能够理解一团跳动的草的异常性——不理解便无法认知,无法认知的现象便会被诡忽略或者遗忘。当然,人类也会如此,在“特部”(特殊事项警戒研究部)中被称为Ⅱ型心因性失忆症(简称二忘)。
领头的一撮草在距离成皜数米远的位置停下,一个小巧的圆环竖立着滚向成皜。
没想到队长也来了,成皜感到一丝惊讶,他看了看自己光秃秃的手腕,有些难为情。不过并未犹豫,左脚开始用力蹬右脚的军靴。
滚落的小环便是队长的诅咒——说谎者的枷锁,将它套在指节上,能够禁锢说假话的生物,是队伍中识别身份的一种有效方法。在验证话语中,被检验者要表明身份、立场,并附带一句假话,以此确保枷锁的正常和说话者的身份。
成皜终于将右脚的军靴脱下,他用脚趾将圆环勾住,套上。
“我是第四队,21,成皜。”
“我永不背叛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并非诸华。”第三句话一出口,成皜便被迫躬身,诅咒的枷锁迅速蔓延,令他动弹不得。
不远处的几簇草轻轻蹦了蹦,来到了成皜身边。大团的草快速包入了他,成皜看到了一个高大的中年人无奈的将他脚趾上的圆环取下,套在了舌尖。另一个青年扶起了他,将一小瓶绿色的汤汁灌入他的口中。
酸涩的汤汁入喉,莹莹绿光包裹了成皜。其他队员有序的将他扶上队长的背部,用螺旋救助绳绑好。
一队草球离开了,他们蹦跳着,踏上未知的归途。
//
雨捕捉了漂浮的灵魂,他们推进着一个残缺的头颅,晃悠悠的在积水中滚动。
张希醒了,不过现在他成为了雨的一部分,这没什么不好的。现在,他正看着蜂拥而至的雨水击打着自己的头骨向一个方向艰难的滚动,莫名生出了一丝看蚂蚁搬家的奇妙既视感。
“咕嘟,咕嘟嘟。”张希的下颌骨磕到了水浅的地面,将他心爱的虎牙碰掉了。指甲盖大小的牙齿沉入水中,不一会儿便被侵蚀消融。
“雨是天幕垂落的风铃,它叮叮咚咚地敲打着不知名的歌谣,在这清幽的曲调中,它取下我的牙,融化我的骨,放逐我的灵魂,让我无聊到在这里鬼哭狼嚎。”
“哎。”张希感到了一丝无奈,在惨痛的歌唱了诡异的、不成调的歌剧之后,张希再次陷入了无事可做的境地。在雨中,他无法离开自己的头太远,同样无法触及任何物体,唯一的变化就是自己的、像灵魂一样的身躯在由透明慢慢变黑。
“完了,”张希促狭的想到,“该去打南北战争了。”
这只是句玩笑话,但张希真的变成了小黑——一个黑色的人影。
黑色的影行走在雨中,他拾起了颅骨,又妄图出没雨水,但他是真正的、不知为何而投射的影,他依托于雨而存在,却无法触及这片区域的一切——除了不属于这里的、张希自己的头骨。
黑影的头消失了,遵循着光路的规则。低下头的张希观察着自己的腿,还有那双自水面截断,又映射在积水表面的长影。
他走动了,良好的走路习惯破坏了影,他拉长手臂、扭转腰腿,他折合成六边形,又转为长方体。
张希不再摆臂了,他略显僵硬的走着,让他更像一个人的影。
雨水淌过已不存血肉的骨,汇成细细的流。黑影甩了甩头,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又甩了甩。
咯吱——叮!一片黑色的泥土,一个收音机,一个人在吃饭。
意外而又喜剧的画面引来了雨中的影,他直直的站着,树立在专注于啃食着收音机的人类的前方。
或许他在进餐,又或许是苦中作乐。他像是衣衫褴褛的济公啃抽鸡腿般津津有味的啃着一台生锈的收音机。黑影看着他,即便无从分辨面孔,但停滞的影在雨中证实着专注的美德。
收音机回收家停止了他的行为艺术,常人无法理解他的思想——或许是不愿被当成美食家围观,或许是想向呆傻的黑影表述他举止的深意,他开口了。
可惜,张希没听到。他能够听到连绵的雨声,能够听到收音机被拆解的叮铛声,却无法倾听艺术家的呐喊。或许艺术家并没有发声呢?他在无声的呐喊,指手画脚的咆哮?张希明白了,这是一种隐喻:只有收音机能够表述一切的、所谓的真相,却少有人在乎当事人的经历呢,聆听着总是被愚昧的圈禁在媒体传播的华丽谎言之中,无知者的声音是雨点,吞噬着苦难灵魂的哀鸣。
他大抵是疯了,他吃着收音机,用憎恶化作牙,狠狠的咬碎收音机,将全部的留言吞入腹中,同时期许着,获得和一个生锈的机器同样的发声的权利。
他吃完了,荒唐的行为终于引来了一个黑影 ,他或许是云端的权柄,又或许只是一位无声的看客?他不清楚,但他必须呐——咆哮般的呐喊!他流血的往昔,他积郁的愤怒,他——倒下了。
//
“我**,我真是**饿急眼了,咋**把收音机给吃了。我肯定是中邪术了,这小可爱怎么还屏蔽脏字呢,我**,还遇见个‘智慧’看我啃收音机,你看**呐。”
“废了啊,我**成电报机了。啊!我*了。”
“我*,*字也屏蔽,si。啊,我si了。”
他倒下了,坚强的艺术家倒下了。张希心痛的看着他无力的在积水中平躺,自己却只是一个黑影无能为力。
该离开了,张希不得不离开了,他感受到了雨的前进,或许是因为驻足观看这位艺术家的表演的缘故,他清晰的认识到了雨的方向性。
他应该是无法离开雨的,因为他只是雨中的影,失去了雨,或许影也会消亡。
张希离开了,像一个雨中的幽灵飘忽着向某处前进。地上的艺术家也爬了起来远远的跟着黑影。
雨漫过了黑色的土地,漫过了稀疏的植被,润湿了一个木质的小渔船和船边倾斜的、干涸的土地。
张希被迫触摸到了小渔船——他被绊倒了。黑影本以为他是影子,但破破烂烂的小船证明了“唯心物理学”的存在。
张希平躺在小船的腰木上滚了滚,像一条扭曲的水草缠绕在小船上。幸运的是他找到并穿上了一件遗弃在小船虾尾部位的蓑衣,又从船板的缝隙处找到了被夹住的破斗笠。
带上了斗笠,张希再次尝试了在床上翻滚。龙须草编织的蓑衣卷成了一卷,但影子戴的斗笠完成了翻滚——因为它圆。
为了让雨和艺术家不必沉默的等待,黑影向着未知的方向走去。可惜,一个茶楼,一位热情的稻草人在行走了几百米后拦住了穿蓑衣的人影。
茶馆是冷清的,没有任何生命再次驻足,即便它兼具历史的沧桑感和雨中伫立的清幽感,却没有客人——能够领悟它所蕴含境意。
热情的稻草人很热情,它狂甩的扫把头、蹦跳的拖布棍腿,每一种动作都证明了它是一位优秀的茶楼招待。或许你会质疑它是否是因为那件写满了故事的蓑衣才发出同病相怜的邀请,但以“衣”取人大抵算不得坏事。
黑影带着他的头颅,走入了茶馆。
天干物燥,是该品一杯清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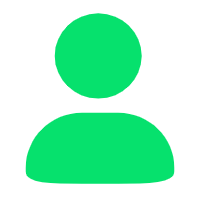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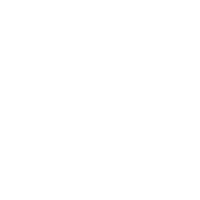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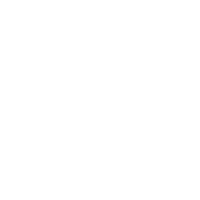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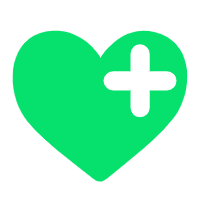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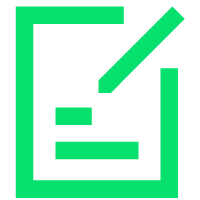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哦,快来首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