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离人归,饮马渡秋水
叶书来担心苗纤纤一时口快,说漏了付朗尘的去向,忙伸手将她往身后一拉,仰首对半空中道:“人一定还在城中,不如再多给几日,这外面围得跟铁桶一样,难道人还跑得了吗?”
如今只能用缓兵之计,盼多拖上几日,拖到付朗尘回来,但显然,叶书来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龙背之上的孟蝉一拂袖,幽蓝瞳孔陡然冷厉:“那他人呢?叫他来见我,我要听他亲口说!”
这可问到点子上了,叶书来一时语塞,身后的苗纤纤又钻了出来,快声道:“付大人生病了,生病了!”
“病了?”蓝眸一厉,长发飞扬,“是和旧情人一同躲了起来吧!”
她周身戾气大发,喝声响彻长空:“快叫付朗尘出来见我!”
苗纤纤傻了眼:“这、这……”
叶书来赶紧又将她掩至身后,慕容钰上前一步,急声道:“孟蝉,孟蝉你冷静点,我们真没骗你,我跟付朗尘那厮可是死对头,我犯得着替他说话吗?他是真的病得床都起不来了,前些日子那样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的,我身子都有些撑不住了,遑论他那小白脸呢……”
初一红袍一扬,拉过孟蝉,哼道:“姐姐,不要跟他们啰唆了,咱们今日就将这结界一举破了,把这些人统统杀光!”
孟蝉眸中蓝光闪烁,周身戾气越来越盛,她终于十指尽伸,掌心陡然散出冰寒之气:“让他来见我!”
这一声凄厉无比,风雪骤然笼罩整个皇城,跪在地上的人们冻得牙齿打战,有稍微起得晚了些的,膝盖上便立刻结了层冰碴儿,睫毛更是瞬间染霜,所有人吓得肝胆俱裂,纷纷踉跄逃命而去。
而半空中的孟蝉还在催动冰寒之气,一双蓝眸狂态尽显,乱发飞舞,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来得猛烈!
她情魄虽丢,但对付朗尘牵绊已深,说是恨意也好,说是执念也罢,总之在戾气驱使之下,竟全然不顾一切,连守住结界的紫薇道君都悚然一惊,急忙运转真气,咬牙继续死死支撑。
长空之下,叶书来一手拉住苗纤纤,一手拖着慕容钰,冻得嘴皮子打哆嗦:“快,快走,咱们先回去,再不走会冻死的!”
慕容钰尽管也冷得浑身剧颤,却仍是不住回头仰望半空,眼眶有热流涌上:“孟蝉,你再等等,再等等……”
白鹤停在洞穴外,化为人形,与付朗尘才略一靠近,便感受到里面传来的强烈波动。
白砚一个趔趄,按住胸口:“不行,我乃妖身,对这洞穴的感应太强,我若进去,定会激起战魂吞噬,犹如猎犬闻到血腥,叫他们蠢蠢欲动,反将你连累了……”
付朗尘连忙扶住他:“你师父也是这么说的,进去的能量越多,洞穴动荡得就会越厉害,那些游荡的战魂就会越发兴奋,一窝蜂拥上来,反而阻碍前行。你就在外头等着我好了,左右我有你师父的血印护身,又是凡胎肉体,只要尽量减小动静,缓慢前行,不会出事的。”
叶书来担心苗纤纤一时口快,说漏了付朗尘的去向,忙伸手将她往身后一拉,仰首对半空中道:“人一定还在城中,不如再多给几日,这外面围得跟铁桶一样,难道人还跑得了吗?”
如今只能用缓兵之计,盼多拖上几日,拖到付朗尘回来,但显然,叶书来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龙背之上的孟蝉一拂袖,幽蓝瞳孔陡然冷厉:“那他人呢?叫他来见我,我要听他亲口说!”
这可问到点子上了,叶书来一时语塞,身后的苗纤纤又钻了出来,快声道:“付大人生病了,生病了!”
“病了?”蓝眸一厉,长发飞扬,“是和旧情人一同躲了起来吧!”
她周身戾气大发,喝声响彻长空:“快叫付朗尘出来见我!”
苗纤纤傻了眼:“这、这……”
叶书来赶紧又将她掩至身后,慕容钰上前一步,急声道:“孟蝉,孟蝉你冷静点,我们真没骗你,我跟付朗尘那厮可是死对头,我犯得着替他说话吗?他是真的病得床都起不来了,前些日子那样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的,我身子都有些撑不住了,遑论他那小白脸呢……”
初一红袍一扬,拉过孟蝉,哼道:“姐姐,不要跟他们啰唆了,咱们今日就将这结界一举破了,把这些人统统杀光!”
孟蝉眸中蓝光闪烁,周身戾气越来越盛,她终于十指尽伸,掌心陡然散出冰寒之气:“让他来见我!”
这一声凄厉无比,风雪骤然笼罩整个皇城,跪在地上的人们冻得牙齿打战,有稍微起得晚了些的,膝盖上便立刻结了层冰碴儿,睫毛更是瞬间染霜,所有人吓得肝胆俱裂,纷纷踉跄逃命而去。
而半空中的孟蝉还在催动冰寒之气,一双蓝眸狂态尽显,乱发飞舞,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来得猛烈!
她情魄虽丢,但对付朗尘牵绊已深,说是恨意也好,说是执念也罢,总之在戾气驱使之下,竟全然不顾一切,连守住结界的紫薇道君都悚然一惊,急忙运转真气,咬牙继续死死支撑。
长空之下,叶书来一手拉住苗纤纤,一手拖着慕容钰,冻得嘴皮子打哆嗦:“快,快走,咱们先回去,再不走会冻死的!”
慕容钰尽管也冷得浑身剧颤,却仍是不住回头仰望半空,眼眶有热流涌上:“孟蝉,你再等等,再等等……”
白鹤停在洞穴外,化为人形,与付朗尘才略一靠近,便感受到里面传来的强烈波动。
白砚一个趔趄,按住胸口:“不行,我乃妖身,对这洞穴的感应太强,我若进去,定会激起战魂吞噬,犹如猎犬闻到血腥,叫他们蠢蠢欲动,反将你连累了……”
付朗尘连忙扶住他:“你师父也是这么说的,进去的能量越多,洞穴动荡得就会越厉害,那些游荡的战魂就会越发兴奋,一窝蜂拥上来,反而阻碍前行。你就在外头等着我好了,左右我有你师父的血印护身,又是凡胎肉体,只要尽量减小动静,缓慢前行,不会出事的。”
白砚思虑片刻后,点点头,握住付朗尘的手关切道:“那恩公你一定多加小心,如果感觉血印跳动不止,似要失效一般,就赶快出来,千万不要执拗!”
付朗尘一顿,对着白砚的眼睛,到底说了声:“好。”
他深吸口气,转过身去,轻轻掀开洞穴外茂密的藤蔓,在迎面而来的阴冷劲风中,迈出了第一步。
才一踏入洞中,就有各方力量拉扯他一般,他身子几个踉跄,差点就要栽下去,好不容易稳住呼吸,一点点抬头望去时,付朗尘几乎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人间炼狱,他脑中只闪过这四个字。
似瞬间跌入了血流成河的沙场之上,眼前满是血染戎装的将士们;有残肢断臂的少年小兵,有脑袋被削了一半的精壮汉子,还有挂着一只血淋淋的眼球,茫然四处张望的先锋军,仿佛想寻找自己跟随的主帅……
耳边仿佛响起尖锐的号角声,厮杀的战场上,马蹄纷乱,鲜血四溅,累累白骨成堆垒起,火光滔天,生灵涂炭。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个坟冢究竟埋葬了多少条性命?
不甘、愤怒、怨恨、痛苦、绝望……无数幽怨戾气扑面而来,将人团团笼罩,胸口一阵阵沉闷难以呼吸,眼前那些虚幻游荡的战魂里,更是夹杂着无数惨厉的哭喊之声,叫人闻之心碎,脑仁犹如巨雷撞击般疼痛难安。若不是有紫薇道君的血印护体,付朗尘只怕早已被这炼狱之景摄去了心神,吞噬了魂魄。
他死死咬住手背,疼痛传至周身,极力调整紊乱的呼吸,胸膛起伏间,过了许久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额上的血印鲜艳闪烁,像一个隐形的结界般,牢牢罩住付朗尘,让他小心翼翼,避开那些游荡的战魂,一路穿行至更深处。
虽有庇佑,但洞中怨气实在太大,付朗尘一边走着,一边太阳穴还是不住跳动,灵魂像被撕扯般,疼得厉害。
他并未受战魂攻击,肉体凡胎尚且如此,那当日陷入洞中的孟蝉与初一,又究竟是受了多大的苦呢?
耳边骤然传来那夜付府上空,骑在龙背上的红袍少年,充满戾气的声音:“谁说我没有死,我是从地狱爬出来的,是早已死过一次的怪物!”
付朗尘闭了闭眼,不敢再去想,稳住心神,咬紧牙关,继续前行。
有些敏感的战魂似乎察觉到他的闯入,开始往他的方向聚拢,付朗尘心口扑扑直跳,脑仁也疼得越发厉害了。
他不敢再迟疑,眼睛抓紧扫过洞中每一处角落,祈盼能找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洞中犹如炼狱的血腥场景,连眼睛瞧着都受不了,像被针刺到般,隐隐作痛,付朗尘一双眼不一会儿就涌上了血丝,但他不敢闭上眼,不敢再浪费一分一毫的时间。
越往洞里走,弥漫的怨气越强烈,也有越来越多的战魂靠近付朗尘,他几乎已经举步维艰了。
尽管有血印护体,战魂即便将他团团围住,也无法真正吞噬到他,但那些滔天的戾气却是真真切切的,让人犹如跌入不见底的深渊之中,连呼吸都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付朗尘仿佛走在刀尖之上,每一步都淌着灼热血珠,从脚到头传来撕心裂肺般的痛楚。
他紧紧握住双手,睁大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避开战魂的围拦,咬紧牙关地找寻着孟蝉的踪影。
终于,他眸光一亮,看见了最角落里面——
一团虚影埋头抱膝,长发散落下来,周身笼着微薄的光芒,身形纤秀瘦弱,没有可怖的戾气,只有一种孑然可怜的瑟缩,正是他心心念念已久的孟蝉!
付朗尘眼眶一热,心头登时跳动起来,赶紧就要提步上前,却被几个高大的战魂挡住了前路。
这几个战魂看起来铠甲最破旧,朝代最久远,戾气最深,说不定就是这洞中第一批被坑杀的战俘!
他们不似前头那些战魂好“打发”,即便碰不到付朗尘分毫,也不停聚拢而来,张牙舞爪着,骇然叫嚣不已,仿佛要在付朗尘的结界上生生撕开一个大口子。
付朗尘瞳孔骤缩,脑袋剧烈疼痛起来,一阵阵恶心眩晕感涌上,叫他根本无法前行。
他抱住头,身子颤得厉害,但一双血丝满布的眼却始终死死盯向前方,盯着那个角落里的纤弱身影。
不行,孟蝉还在等着自己,还在等自己带她离开,带她回家,自己不能就这样被打败,不能被吞噬,不能放弃,绝不能……
想到这儿,身体仿佛涌上一股无穷的力量,付朗尘平稳住呼吸,直起腰身,借助额上闪烁的那点血印,开始打量起围住他的战魂们。
他们的铠甲沾满血污,破旧不堪,但依稀还能辨出上面的字样,那是一个“黎”字。
付朗尘心头一动,脑中飞速运转起来,千百年前,被坑杀在这里的战俘,瞧这装束,面目轮廓又如此深邃,难道是黎族人?
往上追溯千百年,当时的王朝是南诏国,黎族曾是南诏国靠近西北边境,最骁勇善战的一个小族群,那里有自己独特的民风与文化,人人高鼻阔目,模样也与南诏寻常百姓不同,但在千百年前,这一股族群便已灭绝。
想来战火连天,再骁勇善战的民族也敌不过滚滚历史的车轮。
付朗尘眉头紧锁,不断在脑中搜寻着曾经看过的那些史料记载,祈盼于在浩瀚典籍之中寻到只言片语,解当下之困,忽然,他脑中灵光一闪,想起什么般,霍然抬头:“我知道了!”
这声音一出来,付朗尘周围的战魂便纷纷侧目,戾气动荡得更厉害了,有越来越多的战魂不断拥来,付朗尘却强自稳住心神,试着开口唱道:
“离人归,离人归,离人扛旗望故乡,檐头乌鸦溪上荇,开门照我梳妆镜,皑皑白云酿酒行,壮我儿郎前路兴,此去雪山赴沙场,擂鼓十万斩阎罗……
“离人归,离人归,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征人三十万,回首月中看……
“离人归,离人归,岁岁愁扳折,依依绾别离,独夜寒塘梦,相思愁白苹,几经金海雪,不见玉关春……”
他声音本就带着特殊的魔力,又经他这样婉转动人地唱出,周遭战魂们一下顿住了,似乎竖耳倾听,不再有所动作。
付朗尘心下一喜,知道自己果然赌对了,这些果真是黎族的士兵!
他唱的正是黎族的送别曲,这曲在黎族街巷传唱,三岁小儿都耳熟能详,曲名就唤《离人归》,不仅是曲名,还是黎族一种特产的酒名。
因黎族男儿多豪迈,常上沙场建功立业,每到出征前,家中的慈母娇妻就会来到渡口,为他们鸣响鞭炮,开酒饯行。
酒唤“离人归”,唱的送别曲也唤《离人归》,实乃包含了家人们太重太深的祈盼,只愿在外的游子平平安安,早日归乡。
付朗尘一边唱着,一边心思急转,光凭一首曲子,恐怕是不够的,得唤起他们心中对亲人最深切的牵挂,唤起人性中那些久违的柔情温暖来,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些战魂身上的戾气稍许化解一时。
该从哪个方向下手呢?
付朗尘脑中拼命想着,目光却快速扫过一圈,只见围住他的黎族战魂们,个个都极为年轻,最大的看起来也才不过二十,最小的可能十五都未满,大部分都十六七岁的模样。
忽然有什么在他心中隐隐成形,有了,这样年纪的小兵们,不一定人人都有在家等候的娇妻,但一定都有在渡口眺望的慈母。
母亲,一定是他们心中最柔软的那根弦,尤其是他们还这样年纪轻轻,便战死沙场,坑杀于坟冢之中,最委屈最不甘,最想与人倾诉的,也一定是投入自己母亲的怀抱。
想到这儿,付朗尘不再迟疑,直接锁定了战魂里看起来年纪最小的一个,对着他清了清嗓子,放柔了声音,一字一句道:
“你阿娘送你走时,恰是草长莺飞的三月天,她包了黎族满满的蔷鱼饼让你带上,你是她最疼爱的小儿子,她满眼含泪,千般不舍,抱你入怀,揉住你的头哭了又哭。她说,儿啊儿,你怎么穿得这么单薄啊?阿娘舍不得你啊,你何时才能回来啊?阿娘熬着东菇汤等你啊,儿啊儿,斐拉珠带上了吗?数着一颗又一颗,那是阿娘求来保佑你的,数完你就平安回来了,阿娘等着你啊……”
蔷鱼饼、东菇汤都是黎族的特色食物,还有那斐拉珠,更是黎族一种平安吉祥的象征,几乎家家儿郎到了成年的时候,母亲都会亲自为他求来,给他戴上。
果然,付朗尘这首曲子一出来,围住他的战魂们个个伸出手,不由得往脖子上摸去,眼睛瞪得大大的,但那里当然空落落的,什么也不会有,即便有,也早就在战场厮杀中遗落破碎。几乎在同一时刻,那些明明没有了情感的战魂,居然望着虚空,露出了哀楚之色。
付朗尘继续趁热打铁道:“儿啊儿,阿娘给你做衣裳,年年做,年年锁进箱柜里。儿啊儿,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啊?阿娘眼睛都熬瞎,泪水聚成沙,为什么还是等不回你,见不到我的儿啊……”
最后那句“我的儿啊——”,付朗尘刻意拖长了音,还仿了点老妪音色,一时间凄凉无限,仿佛真有一个等到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站在渡头,拄着拐杖,揣着做好的衣裳鞋袜,抻长脖子张望着,一双布满皱纹的眼睛混浊含泪,却永远也等不来自己疼爱的小儿郎了……
战魂堆中不知是谁,发出了第一声啼哭,悲伤瞬间蔓延开去,一个接着一个,哭声此起彼伏,渐渐呜咽一片,戾气不知不觉间尽数消散。
这些千百年前的少年郎,瞪着通红的眼睛望着虚空,似乎在遥望家乡的方向,哭得就如一个个懵懂稚童,嘶哑悲恸,令人心酸不已。
离人归,离人归,离人再也无法归家了。
他们饮下烈酒,赴远方,闯烽火。
也曾望着满天星斗,执着地辨认着家乡的方向;
也曾醉卧沙场,叹古来征战几人回;
杯中雪,手中蝶,唇边话,那些曾经开到盛大的繁华,到头不过万事俱空,灿如烟花,短如流星,在岁月长河中湮灭了无。
唯有那份归乡的执念,刻骨铭心,是他们永恒的支撑。
归乡时,正是黎族琼花开满的季节,他们的慈母妻儿会采花酿酒,与他们在树下对饮,看斜阳照水,风吹河岸。
那是多么美好的场景啊,像梦一般,与如今这人间炼狱,不辨面目的怪物日子截然不同。
心中的那些柔软被彻底唤醒,久违的眼泪冲刷了戾气,战魂们游荡开去,嘴里含糊喊着:“回去,回去,回家乡,见阿娘……”
付朗尘置身结界光圈中,眼眶却也不知不觉湿润了,他声音更加放柔,安抚道:“放下执念,放下戾气,魂归故里,回到亲人的身边……”
待到最后一圈战魂也散去时,他总算松了口气,望向最角落里的那个纤秀身影,情难自已:
“孟蝉,我来了,阿七来带你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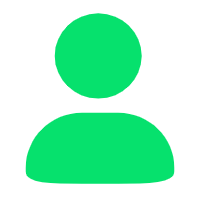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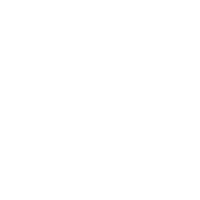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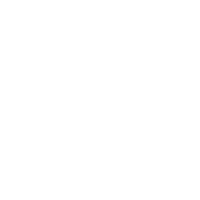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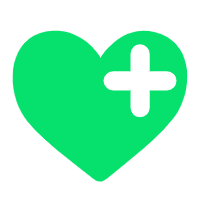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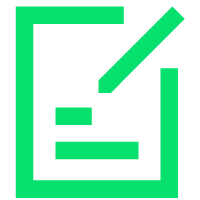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哦,快来首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