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找宝藏,我则开始寻找逃跑的路径。后来让我寻到机会,逃脱了出去。我知道是有人帮我的,光凭我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这么轻易逃脱。抓我的这帮人之中,还藏匿着其他势力的暗桩。果不其然,我刚逃出去,就被这个暗桩带走了。他告诉我,抓我的人是东厂中官张鲸,而他是恭妃的人。”
“恭妃!”孟旷吃了一惊,恭妃王氏是当今皇长子之母。今上登基后,围绕着立储的问题,皇长子与皇三子已然争了好些年,事关恭妃,事情立刻就更加复杂了。
“那暗桩告诉我,恭妃和皇长子在外的势力不强,能帮我的很有限,甚至根本不敢直接与张鲸的人起冲突,只能暗中救我出来。为今之计,我必须想办法入宫,只有入宫,我才能保命。”
“那暗桩是谁?”孟旷追问道。
“方铭,当时只是南镇抚司的一个总旗,后来听闻升了南镇抚司的副千户。我后来才知道,南镇抚司有相当一批人是张鲸的人,专门做他打手,方铭也是其中之一,但他其实是恭妃和皇长子安插在张鲸身边的人。”穗儿答道。
孟旷点头,她知晓此人,因他也是当下十三太保之一,行十二,尚排在孟旷之前。诨号“典校郎”方十二,是锦衣卫内难得的文雅人物,且对锦衣卫庞杂繁多的内部人员情况一清二楚,活似书库的典校郎一般。
穗儿顿了顿,低下头来道:“我当时别无他法,便只能听从方铭的安排。他悄然带我入宫,买通了尚服局的司衣,将我加入了当年新入的一批尚服局刺绣宫女名单之中,化名惠儿。此后数年,我留在宫中,张鲸曾查到过我的下落,我为求保命,拼死博得太后看重,指名要我制衣,张鲸才不敢明着动我。宫中尔虞我诈,暗箭难防,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挣扎保命,数度差点被阎王索命,无数次死里逃生。一直到万历十六年,张鲸圣前失言,被罢官归乡,彻底失势,我才能够获得些许喘熄。此间,恭妃数度找到过我,也问过我有关那笔传说中的宝藏的事。但因为张鲸搜索多年无果,恭妃也不能确认我的想法是否是正确的,宝藏之事自此成迷。唯一的办法,就是寻到现在仍然幸存的张家人,从他们口中得到些许消息。
此后又过了四年,也就是前段时间的事,恭妃和皇长子派出去寻找张氏子弟的人终于传回消息,说是找到了五郎张允修。但是张允修声称他也知道得不完全,只知道一部分拼接图纸的口诀密钥,另有几段密钥,张氏兄弟分别掌握。如今张家长子二子均已死,还剩下三子、四子和五子天南地北苟延残喘。而当年那批绣品已然被焚毁,我是唯一记得全部图纸的人。他必须亲眼见到我,让我当着他的面画出图纸,他才能按照我画的图说明图中的奥秘。据传回的消息,张允修双足有疾,已然不能长途跋涉,现如今人在大同。所以恭妃才安排我悄悄混出宫去,赶往大同与张允修会面。但不知怎么消息泄漏了,我出宫后,恭妃安排送我去大同的人没有出现,反倒有一群陌生人一直在跟踪我,我不得以拼命跑出城去,一路快速向西北方向逃亡,不巧遇上大雪封山,只能逃上了妙峰山。之后的事,你都知道了。”
她三两句话云淡风轻地就把九年间的事儿说完,好似非她亲身经历。可闻者孟旷内心深处却听得心惊肉跳,这些年穗儿所经历的事,当真是一波三折,步步惊心。孟旷一时有些悔意,自己似乎不该把家人死去的仇恨怪罪在她头上。可是,她这心里恨了这么多年,一时之间,却又扭转不过来了。
她有些别扭地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闷声道:
“如此说来,害死我父兄的人,应当是张鲸了。”
“若不出意外,应当是他。”穗儿道。
孟旷咬牙,寻寻觅觅九年时光,她终于确认了杀死父兄的仇人所在。眼下张鲸退废林下,人在杭州,路远迢迢,她身为锦衣卫也不能乱跑。该如何报家中血海深仇,还有待计划。
穗儿见她满面仇恨难以掩饰,终于鼓足勇气问道:
“当年你父兄去世后,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何以如今搬到了这里?”
孟旷被戳中痛处,一时唇角下撇,面容悲戚。她虽不愿回忆惨痛的过去,但还是决定把家中发生的事和穗儿简单说说。于是整理思绪,组织语言,随后终于开口叙说。
第13章
“你们走后第五天,巡捕营的人找到了我们家。当时我去了城外打樵,只有母亲、二哥和小暧在家。巡捕营说有郊外的村民在田埂里发现了两具男尸,报了官。仵作勘验后,有吏员认出可能是锦衣卫稽查所副千户孟裔与其长子孟旭,现在需要家里派人过去认尸。据我二哥后来跟我描述,娘亲和小暧都吓坏了。他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即便身子不好,也要扛起责任。二哥和娘亲把小暧送到了大舅家,然后大舅陪着二哥、娘亲一起随巡捕营的人去了停尸的顺天府衙。看到尸体时……娘亲大受打击,当场犯了喘疾,眼看着要不好,我二哥也是天旋地转差点要晕倒。大舅慌忙让人去请大夫,但是大夫赶过来时已经迟了,我娘亲就这么过去了……”
孟旷说到此处,一时说不下去,下唇在轻轻地颤唞,眸光中凝着一股深沉的哀痛。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有千钧重,沉沉地压在穗儿心头,让她喘不过气来。
孟旷沉默了一会儿,压下一时涌起的情绪,才继续道:
“我们是一日之间一下失去了父亲、母亲和大哥,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就像天塌下来一样。记忆里,好像我能撑下来,是因为还有二哥在。他那么病弱,却为我和暧儿扛下了所有的重担。还有大舅和表哥,忙前忙后,一手操办了丧事。最后出殡时,我强迫自己仔细查看了父兄的尸体,他们是被乱刀砍死的,身上全是皮开肉绽的刀伤。据仵作说,他们身躯僵硬,皮肤苍白,是失血过多之状。人大概是死于四日前,因为天寒地冻,所以尸体并未腐坏。死时手中还握着武器,应当是战斗到了最后一刻。那片田埂是抛尸地,战斗现场在三元驿附近的一片丘陵之中。为何凶徒会抛尸,至今原因不明,官府猜测凶徒可能是附近的流民,杀人的目的是抢劫,而战斗地应当是他们的聚集地,他们害怕官府查过来,遂抛尸转移注意力。
但是我后来查过,那里根本就没有流民聚集,官府的解释根本是胡编乱造,只是为了应付了事。我父亲和大哥都是锦衣卫,他们的死,在锦衣卫内部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的锦衣卫指挥使刘守有迫于内部压力,专门派了人去细细查过案发现场一带的情况,怀疑可能与三元驿附近聚集的劫掠商旅的匪帮有关,那附近混有不少山东的白莲教匪帮,凶悍无匹。任我父兄如何身手了得,也是双拳难敌四手。但是再往下细查,困难重重,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如今看来,他分明是贼喊捉贼,他与张鲸沆瀣一气,我父兄就是被他害死的!”
孟旷怒然一掌拍击在桌面上,“嘭”的一声巨响,桌腿与桌面榫卯处一下多了一条裂纹。穗儿被她这一掌吓得惊起,心脏怦怦乱跳。
屋内在这一声巨响后陷入沉默,穗儿煞白着脸小心翼翼地抬头看孟旷。但见她双目赤红,眸光闪烁波动,似是在痛楚地思索着什么。不一会儿,她将眸光投向穗儿,穗儿当即低下头去,不知为何不敢与她对视。
“抱歉,我吓到你了吧。”孟旷有些生硬地说道,穗儿能听出她的别扭。
她摇了摇头,然后又问:“为何……你会替了你二哥?你二哥呢?”
“他现在何处,我亦不知晓。”孟旷缓缓道,“我家世袭军籍,父兄死后,需要有人来袭我们家的军籍。照道理,便是轮到我二哥,但我二哥身子羸弱,根本不能去当兵,那会要了他的命。本来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花钱寻一个人替二哥去服役,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父兄死得太蹊跷,我们兄妹三人一致想查明他们的死因,而此事背后牵扯甚广,若我们只是一介平民,难以接触秘辛,唯有进入锦衣卫,才能借助锦衣卫的资源和人脉查明真相。我要替我二哥袭家里的军籍,女扮男装入锦衣卫。二哥为了帮我扮成男子,为我打制了修罗面具和隐藏女子身段的身甲,编造了颞颌惯性脱臼的谎话,帮我先通过了入锦衣卫最开始的体检。他为我袭军籍最后做的一件事就是——离开京城,隐姓埋名流浪外地。
对外,我们宣称孟家三女孟晴嫁去了外地,不久后病逝。我二哥化名孟子修,成了我们家流落在外的一个远房族叔,辗转各地当教书先生或卖字画、替人写信为生。他偶尔会寄信回来,简单写一写近况,字里行间还要刻意用些隐语。我们回信,会给他寄一些钱财衣物。Θ思Θ兔Θ網Θ文Θ檔Θ共Θ享Θ與Θ在Θ線Θ閱Θ讀Θ
这些年他在外,也在不断地查父兄之死,但没什么进展。我最近一次收到他的信是半年前,他人在应天府,最近一年他都在那里,刚到就大病一场,靠着赵氏米行在应天府的几个老伙计照顾,好不容易病愈,只说又要启程。今年元月初,我出任务去了西北,今日才归,不知他最近是否也曾来信。”
她顿了顿,最后道:“我和暧儿从灵济宫的老家搬了出来,搬到了校场口。这院子原本是赵氏米行的,我父兄和娘亲出事后,大舅心灰意冷,加之近些年粮米时艰,难以为继,生意典出去大半,这院子也腾了出来。打扫一番,我和暧儿住了进来。我当时已入锦衣卫,暧儿无人看顾。恰逢当时这丫头萌生了学医的念头,于是罗道长和他的弟子清虚就来帮忙,暧儿拜了罗道长为师,学习医术。暧儿十八岁时,罗道长外出游方行医,将这灵济堂全权交予暧儿打理,留了清虚襄助。方才你见到的那位年轻道士,就是清虚。”
穗儿听她慢慢说完,一时无言以对。
孟旷沉默了一会儿,遂起了身道:“时间不早了,你歇了吧。你这间屋子门窗我都会落锁,有什么事儿需要出去你就喊我,我就在你隔壁。”她指了指不远处的房间内门,原来这间房与南侧的厢房内部是有门互通的。
穗儿看着孟旷把这屋子内的窗户一一落锁,终究忍不住道:
“为何这般锁着我?我也不会逃。事到如今,我已经无处可去了。”
“我不知你是否当真无处可去,锁着你,是为了查明真相。”孟旷淡淡道。
“你不信我……”穗儿抿唇。
“抱歉,我入锦衣卫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怀疑。何况你已知晓我家中秘密,干系重大,不锁着你我亦不会安心。”孟旷似乎是一下说了太多,眼下也不愿再多做任何解释,最后带门出去,干脆地落了锁。
穗儿独自一人坐在房里,缓缓抬手撑住额头,幽幽长叹了一声。
……
出了门,外面天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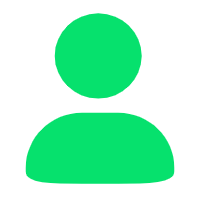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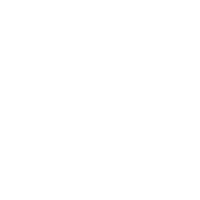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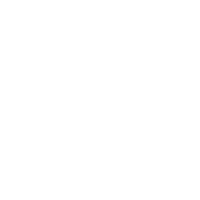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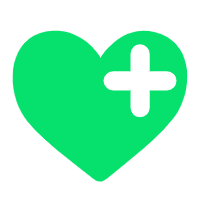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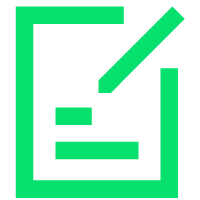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哦,快来首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