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人的主意,我猜想恐怕与那诏狱的黎老三脱不开干系。”
“黎老三和阿爹一起将死囚弄出来藏到家里?这也太古怪了吧,进了诏狱没听说过还能出来的,黎老三可是个吃人的主,更别提他亲自把人救出来了。”孟晴百思不得其解。
孟旷只是叹息,他也是万分疑惑。
“晴儿,这不是个好兆头,但愿不会给家里惹事儿。”孟旷最后说道。
第8章 【旧事】
大约卯初过些时候,孟裔就草草用过朝食出门了,他只着一身粗布衣衫,戴了斗笠,裹了螣刀绑在扁担杆上,挑了两个装满针线活的箩筐出去,瞧上去就像个贩夫走卒。箩筐里有刚纳好的新鞋,有漂亮别致的绣囊,都是赵氏一双巧手做出来的,往日里也会拉到街上贩卖,贴补家用。孟裔出门前反复叮嘱旷晴兄妹闭门不出,掩护好那女娃并照顾好母亲,兄妹俩都一一应下。
送走孟裔,兄妹俩回厨下用朝食,彼时母亲才起身,瞧着身子不大爽利,眼底泛青,恐是昨夜一夜未眠。
孟晴打了热水服侍母亲洗漱,又扶她在餐桌旁坐下,端上炊饼和白粥。孟旷坐在她身边,将酱菜碟子往她身前推了推,道:
“娘亲,您多少吃点吧。”
他这话不说还好,一说,赵氏却默默落下泪来。孟旷和孟晴不由慌了神,孟晴忙道:
“娘亲,这是怎么了,怎么就哭了?”
赵氏半晌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垂泪。孟旷叹息垂首,孟晴只能坐在母亲身边抚着她后背,好一会儿,赵氏终于收了眼泪,取出帕子擦了擦满面的泪水,哑声道:
“旷儿,晴儿,你们大了,都晓事了,娘不瞒着你们。你们爹,这是要把咱家至于危险的境地之中啊。他素来爱护这个家,如今却像是鬼迷了心窍。娘这是害怕啊,他昨儿晚上就像变了个人,怎么说他都不听,带个人回来也不给半点解释。但那女娃子分明是他从诏狱里带回来的,他怎么能做这种事?真让人焦心啊……”
“娘,您莫着急,爹说了,过几日就把人送走了。”孟旷道。
“送走又如何?这事做都做了,一查就查出来,何患无辞?昔年太/祖时蓝玉一案,牵扯出多少人,多少人何其无辜,何况你父亲本就是犯事儿的人,怎么着都跑不了。”赵氏识文断字,也读过一些经史,更是常听父兄私下里议论朝中上下的一些事儿,她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赵氏说得在理,兄妹俩都沉默了。
孟晴想了想,拿了两个炊饼,打了两碗白粥,用食盒装了,拎起来就往外走。赵氏喊住她:
“晴儿你干甚么去?”
“给那女娃还有暧儿送朝食。”孟晴答道。
赵氏蹙眉道:“你这孩子,娘方才的话你可听进去了?”
“娘亲,事情既然都发生了,再如何忧虑也是无济于事。那女娃吃了很多苦,年纪估摸着比我还要小几岁,她犯了甚罪大恶极的事儿要在那炼狱般的地方受苦?既然父亲救她出来,必然是有原因的。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过好咱们的日子,也照顾好那女娃,相信父亲。别的不说,至少咱们自己问心无愧。”说罢笑了笑,便提着食盒往西屋去。
孟晴的一番说辞让赵氏哑然,孟旷却笑了,道:
“娘,晴儿就是乐天这点好。您也别太过忧虑。晴儿那句话说得很对,相信父亲,也照顾好那女娃,至少咱自己问心无愧。”
赵氏叹息,心中却想,孟晴这孩子,太良善了,这将来若是嫁了人,别让婆家欺负了去。如此一想,不由又忧心起来。
……
孟晴提着食盒和装满开水的铜壶进了西屋,打眼一瞧,暧儿还裹着被子在榻上赖床,穗儿却不知何时已经起了。她正坐在床边,默然注视着窗外,神情萧索,全不似她这般年纪的女子面上会有的神色。见孟晴进来,她立刻立起身来,娇弱的身躯比孟晴瘦小了一圈,孟晴的内衫穿在她身上很是不合身。她还是存了些许紧张,双眸锁在孟晴身上,苍白的双♪唇抿得紧紧的。
孟晴扬起笑容,走过来将食盒搁在桌案上,又把铜壶里的热水倒入铜盆,端了青盐牙擦和漱口杯来,道:
“既起来了,就先洗漱吧。”
穗儿点了点头,拘谨地走到水盆架边开始洗漱。孟晴则走到床边叫妹妹起床,小丫头睡懵了,精神不济,一头乱发地被姐姐从床上拉起来,呵欠连连。随后在姐姐的催促下跑到穗儿身边,冲着穗儿嘿嘿傻笑两下,也开始乖巧地洗漱起来。
穗儿的神色柔和了许多,周身的拘谨也松弛下来。一大一小在无声的交流中洗漱完毕,便坐下来开始吃朝食。屋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只有吃饭时碗箸的声音轻轻作响。穗儿恐怕是饿了,吃得很快,但动作却很优雅。孟晴观察着她,觉得她应当是有着非常好的教养的,举止就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一般。虽然她很饿,但她却克制着自己,只吃了一个炊饼,喝了一碗粥,便不再吃了。孟晴也没劝她多吃,等她们都吃完,自收拾了碗筷去厨下清洗。
“我……我帮你吧……”她刚踏出西屋,身后的穗儿就喊住了她。
孟晴点了点头。
二人坐在井边,打了清水洗碗。孟晴偷偷看她,朝阳已出,照亮了孟家小院,金辉洒在她苍白的容颜上,衬得她如梦似幻般美。孟晴心底没来由升起一股奇怪的情绪,团在心口,柔柔密密的,说不出的滋味。她终于忍不住出声道:
“家里住得惯吗?”
穗儿点了点头。
“我爹说,过两日要把你送走,你可还有别的去处?”
女孩面上浮现起惶然的神色,孟晴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话了。
“你没地方去了吗?”
“他要把我送去哪里?”
她们同时说道,随即面面相觑。穗儿瞬即低下头来,面颊涨红,神色忧虑恐惧。孟晴结舌了片刻,笨拙道:
“你莫忧心,我阿爹是好人,他不会害你。”
这话说出口,也不知是安慰了自己还是安慰了穗儿。穗儿神色更加凄然,孟晴心中煎熬,最后硬着头皮道了句:
“若你没处去,就在我家留下,左右不过多了双筷子。”
说完这话她真想掌自己的嘴,这何止是多双筷子的问题,这是关系全家人的性命攸关的大事。孟晴不是不懂事,她明白这个女孩越早离开自家越好。可是看着女孩那凄楚的神色,这句话就不自觉地脱口而出了。
罢了罢了,反正也不是她说了算。
“……若你阿爹要送我走,我也不会赖着不走的,我……不会连累你们的。”穗儿像是为了回报什么,努力地说道。尽管她这话说得很勉强,看得出来她非常恐惧于不可控的未来,她应当仍然对孟裔保留有相当程度的不信任。
二人默默然清洗好碗筷,孟晴接下来要开始每日的功课了。白日里都是她练功的时间,上午是熬炼筋骨气力,下午则是螣刀刀法的习练,一日不能落下。家中虽有新的来客,她也不避讳,便当着穗儿的面练起功来。家中院子里有当初大哥为了炼体留下的一些器械,石锁、铁饼、单杠、重链,练马步的油缸,还有重弓和箭靶。如今这些器械都成了孟晴的专属,每日她都会习练。就在她做热身准备时,孟旷从厨房中出来了,和孟晴打了个招呼便入了东屋开始读书,他也要开始每日的功课了。^o^思^o^兔^o^網^o^
穗儿看着孟晴练功,觉得十分新奇。她还是第一次见到有女子这样锤炼自己的身体的。而且孟晴身稳力沉,体格强健,那些沉重的石锁铁饼在她手中被挥舞得虎虎生风,显然非一朝一夕之功。瞧着她在院子里大汗淋漓地锻炼体魄,穗儿竟看出了神,一时忘却了诸多的烦恼,获得了久违的安宁之感。
不知不觉间,孟暧来到了穗儿身边,搬着小方凳和她坐在一起看姐姐练功。对孟暧来说,这都是习以为常的事了,但见穗儿看得这般入神,她不由起了骄傲自豪之情,道:
“我阿姐厉害吧。”
“嗯,厉害。”穗儿由衷地点头。
“全北京城,我阿姐是最厉害的女侠,女中豪杰。”这小丫头不知道从哪学来的词,对穗儿吹嘘道。
穗儿闻言,不禁对小丫头嫣然一笑。这一笑灿然美丽,摄人心魂。笑容恰好被刚走出厨房来到院子里的赵氏瞧见,赵氏静静地观望了一会儿,叹息一声,默默转身回了北屋休息。
倒也真不是什么坏孩子,也是可怜了……她心想。
这一日,穗儿就这样静静地跟在孟家人身后,按着他们的步调过日子。孟晴练完功,简单去浴房擦了身,就去准备午食。这一日母亲身体欠妥,孟旷读书又到关键时期不肯出来,午食家中人没聚在一起用,孟晴装盘,分别给母亲和孟旷送去屋里,自己则和孟暧、穗儿一起简单用了午食。下午孟暧跑了出去,孟晴午休片刻,又开始继续练功。下午练刀,院中一直充斥着她挥舞螣刀的声响。穗儿被这特殊的兵器和其挥舞起来的姿态所慑,似是想起了甚么恐惧的记忆,面色有些苍白。她兀自归了西屋,未再出来。傍晚时分,孟晴开始做晚食,孟暧跑了回来,不知从哪儿拿回来两块甜糕,用帕子裹着。她与穗儿相识一日,已经结成了良好的友谊,拉着穗儿出了屋子,并肩坐在院子里,将糕点与她分食。孟旷完成了白日的功课,出来活动一下筋骨。他似是在思索着什么,百思不得解的模样。于是入了厨房,对正在做晚食的孟晴道:
“晴儿,我方才读书,观得一句‘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於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你可知出自何处?”
“甚么?”孟晴正在灶上噼啪炒菜,没听清。
孟旷又大声重复一遍,道:“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於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这句出自何处?我瞧着眼熟似是在哪儿读过,却一时想不起来了。”
孟晴想了半天,没有头绪,不得不摇了摇头。此时孟旷身后,厨房门口突然传来了一个清甜的女声,回答道:
“这句出自东汉王充的《论衡》,应当是问孔篇中的一句。”
“是咯!就是《论衡》!”孟旷恍然,顿时又惊又喜,望向身后,却见恰是那女子穗儿。
“你读过书?”孟旷问。
“读过一些。”穗儿点头道,说这话时,她一改之前展现在孟晴面前忧郁踯躅的模样,显出几分傲骨嶙峋的气质来,不卑不亢,面上挂着淡笑。她虽说着标准的官话,可口音仍不可避免显露出些许吴侬软语的腔调来。
孟旷似是有意考考她,又问:“可读过四书?”
“读过。”
“《中庸》第二十三篇你可背得出来?”
穗儿微笑诵道:“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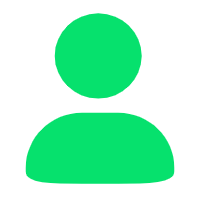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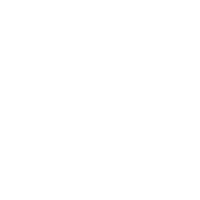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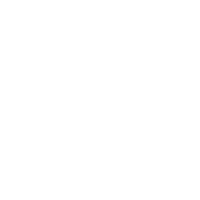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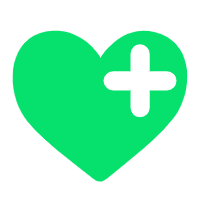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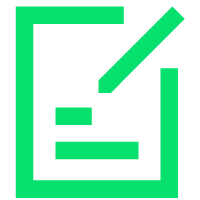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哦,快来首发吧